 交響樂作曲家王西麟近影。圖為他在德國講授音樂。(王西麟提供)
交響樂作曲家王西麟近影。圖為他在德國講授音樂。(王西麟提供)
【編者按】帶著新專輯《山歌寥哉》,刀郎強勢回歸流行樂壇,其作為一種現象,意義遠超出他與「中國好聲音」話語權霸主們的江湖恩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一向曲高和寡的交響樂家王西麟竟也遙相呼應,在德國聽著《羅刹海市》為刀郎叫好,這事說實話是有點出人意料。畢竟,現年八十六歲的西麟老先生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古典音樂作曲家之一,而作為一位卓越的交響樂作曲家,他的創作主要在表現民族苦難和悲劇方面,以一系列帶有強烈顛覆性情感的悲劇性交響樂作品著稱。蔡霞老師有心,親自出面邀約,得西麟老先生欣然命筆,把他叫好的「刀郎現象」娓娓道來。
然後蔡霞老師又想好事多磨些時日,先按著不發,好成人之美,讓西麟老先生的樂評先流入牆內更廣泛傳播。果然,各平台也算盡力了,但為過審,還是不得不刪了個七七八八,聊勝於無。現在終於輪到小義伸展拳腳,推出本文未刪節的完整版,於是特意藉此敲黑板、畫重點,把內網過審時刪掉的部分一一高亮劃了出來。以饗讀者之餘,也可以從中窺見西麟老師觸碰了當下中國文化的哪些G點。
言小義
最近,刀郎的歌成为一个极为突出的重大文化事件,
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刀郎的那首歌。但是从那时又过去了很多年,
为什么说这是极大的好事呢?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摇滚乐现象。1986年,
我是从事交响乐创作的,
摇滚乐是立体的,多声部的,有强劲有力的节奏,
除了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
这里就说到流行歌这个最大最广泛的文化现象。 早在1979年底至1980年初,我正巧在海南岛、湛江、
我想,凡是在八十年代听过邓丽君歌如《丝丝小雨》、《海韵》
十多年以来,崔健现象越来越孤立了,且演出很少。
刀郎的歌出现,
有人说刀郎的歌是影射流行音乐界某些人,
刀郎的歌是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一种犀利批评,
萧斯塔克维奇的第十三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幽默》,
下面再说说对刀郎新歌的艺术评论。 从音乐艺术上来讲,刀郎的歌还有些不足。
一方面,他的和声语言还不够丰富,和声比较单调,
我看到有人把他的节奏排对起来了,排对七个字什么的,
同时,我也希望刀郎这样的歌,这样的队伍,
19世纪的欧洲音乐家罗伯特·舒曼曾高度评价萧邦的马祖卡是“
(2023年8月7日,写于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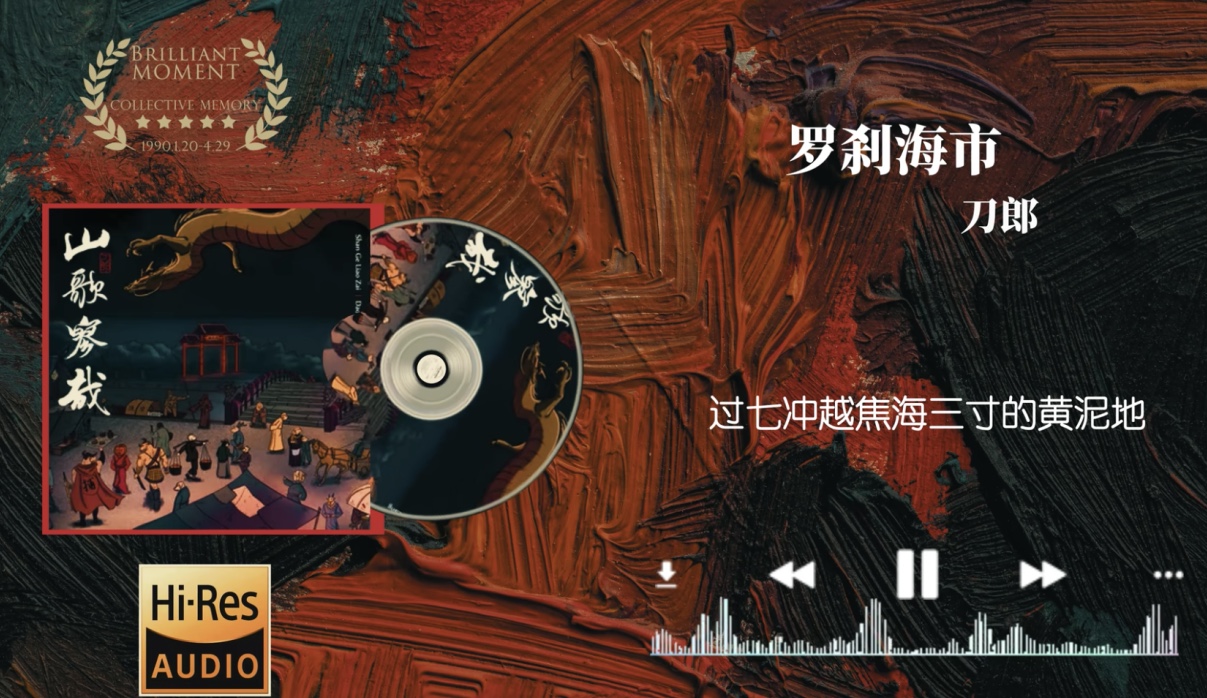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1098】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