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回合:冷战与意识形态的大决裂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声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德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缓缓落下,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二。”这个演说标志着“冷战”的肇始。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正式提出以“遏制”苏联为战略中心的杜鲁门主义。同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启动“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决定连续四个财政年度对西欧各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支持它们战后重建。苏联及其东欧国家对美国的“遏制”战略迅速作出反应,同年9月,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两个阵营”理论,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的政治军事同盟正式形成;1955年5月,苏联及其东欧国家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冷战将欧洲一分为二,也将法国思想界一分为二,雷蒙·阿隆将此定性为意识形态的“大决裂”,米歇尔·维诺克对阿隆提出的这个关键词作了精辟的概括:
“象征着不可调和的两种世界观、两种历史哲学思想、两种生活和政治体制的两大决斗者之间的全球性的对立。”[1]

按照托尼·朱特的概括,在1944年至1956年间,法国知识界对斯大林主义出现了四种反应:第一种就是简单的拒斥,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第二种是简单的接受,以阿拉贡这类法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三种是持摇摆立场,以埃德加·莫兰为代表;第四种态度最为复杂,以萨特为代表,他们不想成为共产党员,却愿意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萨特曾特别强调:“苏联因其目标而拥有特权(为全体的正义和自由),并且,据此区别于任何其他的体系和政权。”[4] 在他看来,西方世界无以提供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因此,在苏联迫使人们通过其在布达佩斯的野蛮行径去直面这种社会主义时,即使感到迷惘,那也是人类别无选择的选择,“没有什么可构想的状况能够使得我们放弃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仰”。[5]

比较而言,萨特所代表的这类共产党的同路人,比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尽管他们也清楚,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和现实的苏维埃政权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但后者毕竟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迈进,他们更愿意为苏联的革命和政权模式提供一种历史的和理论的论证——“苏维埃共产主义本身既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自明的真理的支持,同样也是后者的确证。”[6] 梅洛-庞蒂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选择和萨特站在一起,他在1947年发表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为当时饱受指责的苏维埃政权的暴力和恐怖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辩护,认为“对共产主义或苏联的任何批评”和“对民主政权的任何辩护”都必须置于“整体性”理解之中,也就是“不能通过脱离背景的孤立事实作出判断”。他依据列宁关于不应该把普遍历史的观点用于每一个地方历史的插曲中这一看法,断言苏联目前曲折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总体历史的揭示,也许就显现为唯一可能的道路”。[7]
正是在萨特主导的强大的左翼语境中,冷战在法国思想界所造成的一分为二的后果,不是以北大西洋组织的政治标准来建立一个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向西欧蔓延的统一战线,而是左翼知识分子与苏共及法共结成了政治和思想联盟。
以撰写《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而闻名于世的朱利安·班达,曾经强烈主张知识分子超越阶级和党派之争而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反对被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政治激情”所左右,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普遍性存在的价值在于其是“抽象的公正、抽象的真理、抽象的理性”的象征,“知识分子高扬的就是这些永恒的东西,这些人类的共性”。[8] 但是,在冷战的时代氛围中,班达却完全“背叛”了这个立场,选择相信共产主义,选择与苏联站在一起。他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两个阶级阵营和它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所各自代表的东西之间,法国必须做出选择。”[9] 也就是在苏联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和它的形形色色的敌人之间作出选择。班达和萨特一样——尽管他们始终不和,对法国现实的民主制度的高度不满,转化为对苏维埃制度充满想象和期待,他们把解放工人阶级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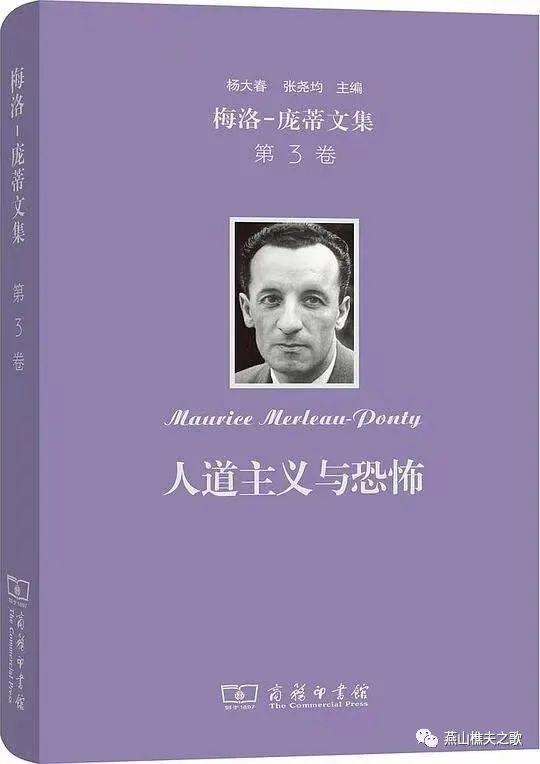
从1945年至1948年,萨特一直是处在被法共点名批判的名单里,而且还成为苏共批判的对象。1948年8月,苏共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召开了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西方堕落”的报告中,对萨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谩骂,说萨特是“会打字的鬣狗,会用笔写字的豺狼”,[12] 萨特成了必须被打倒的假进步主义的典范。然而,正是在共产党人的批判声浪中,萨特反而更加坚定地决心成为他们的同路人。1949年1月法国发生了“克拉夫琴科案”,1950年11月发生了“鲁塞案”,[13] 在这两起著名的案件中,萨特均站在了法共领导的《法兰西文学》的立场上,强烈谴责克拉夫琴科和鲁塞对苏联集中营制度以及各种反人类行为的揭露,指控他们为了抹黑苏联而不惜造谣。1950年1月,萨特和梅洛-庞蒂联名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生命的岁月》,强调他们不想在受害者中间做出选择:在希腊也有压迫,在法国殖民地也有屠杀,为什么要在苏联集中营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这在梅洛-庞蒂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已有阐释:既然“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和德雷福斯事件都没有影响雅典和法国的‘人道主义’名声”,同样,“没有理由要给苏联适用不同的标准。”[14]
萨特迈向共产主义的关键性一步是他在1952年发表了《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文,此文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萨特为了支持法共领导人雅克·杜洛克,后者为抗议美国李奇微将军访法而被捕,萨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用波伏娃的话说是“怒发冲冠”,从而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共产主义阵营。
萨特后来在纪念梅洛·庞蒂的文章中写道:“经过十年的深思熟虑,我终于面临着决裂的时刻,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刺激。用宗教用语来说,这是一次信仰的改变。”[15] 雷蒙·阿隆把这次“改变”视为产生了另一个“萨特”,一个原来信奉存在主义主体、个人和自由的萨特转变为一个信奉集体至上的斯大林主义者。

冷战在战后法国制造的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的巨大错位,即法国在政治上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在思想上却被以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引向了苏联,这充分表明要改变“萨特时代”的错误导向将会是多么的艰难。左翼旗帜下几乎所有共产党的同路人都认识不到雷蒙·阿隆提出的意识形态“大决裂”的迫切性:“苏联把欧洲的一半苏维埃化了。为了维持欧洲的平衡,必须有美国参与,因此大西洋联盟是外交平衡的必需品。”[20] 这意味着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同时也是对势力范围或统治权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对社会政治制度的选择。阿隆提出意识形态“大决裂”,一方面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上的考量,他在1950年柏林举行的世界保卫文化自由大会上指出,要阻止苏联冒险发动新的战争,取决于满足两个条件:“(1)不能让苏联获得某种优势,哪怕是最初的优势,否则冒险的诱惑会令它无法抵挡。希特勒就没有抵挡住这种诱惑。轻信人民之父的智慧将是危险的。(2)阻止苏联在政治上取得成功,这会增强它的力量,从而使所有平衡的希望破灭。”[21] 另一方面,阿隆之所以高度警惕苏维埃政权对于西欧国家的潜在威胁,就在于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极权主义的两种历史形态,当法西斯主义随着纳粹帝国的彻底崩溃而失去其制度性土壤时,欧洲乃至人类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就不是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未来返潮的假设,而是唯一地来自于现实中的斯大林主义。所以,在阿隆看来——
“在20世纪,任何行动都意味着并且导致人们就苏联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在谈论历史的同时,回避历史现实的束缚。”22阿隆毫不隐晦地向世人宣布自己的立场:苏联模式是人类社会的一场噩梦。[23]

1930年,阿隆赴德国留学,在确定未来的研究计划时,其初衷是想促进法德这两个欧洲大国的和平相处,但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运动的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和扩张性必将为欧洲带来一场战争。此时,尼采关于20世纪的预言——以意识形态名义进行大型战争,给他以巨大的理论启示。1934年,欧洲弥漫着浓重的和平主义气氛,阿隆却对此保持冷静。1938年,阿隆出于心理和历史直觉,认为第三帝国的领袖有本事冒天下之不韪,作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这个政权创造的表面上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过了俾斯麦。1939年,阿隆在法国哲学年会上提到德国和苏联这两个极权制度有可能成立联盟。同年6月,阿隆参与编辑的一本论文集《专制时代》出版,他在评论文章中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质性作出了精辟的概括: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地排除一切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公民投票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闹剧,借此叫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主权托付给总揽大权的主子大人。其次是个人自由:德国公民、意大利公民和俄国公民,都没有任何办法对滥用权力的行为提出申诉。公职人员、共产党党员、地方上的纳粹头头、法西斯支部书记,都是上级的奴仆,可是对老百姓却如豺狼虎豹。再就是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科研自由,一切自由都销声匿迹。在英国的民主生活中,有这么一句值得钦佩的话:反对派是为公众服务的,而在极权国家,反对派则犯了罪。”[24]

阿隆虽然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置于同一个极权主义谱系,但在二战前他还是把纳粹帝国作为欧洲的首要威胁,意识到需要借助苏联来对付德国,并且他个人还处在马克思主义的浸润之下,坚守着左翼的立场。到了战后,阿隆承认自己在战前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苏联政权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认为意大利的和希特勒的极权制远远不如苏联的极权制,后者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一是国家吃掉公民社会,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变成教条,强迫知识分子和大学信奉。”[25] 阿隆确认自己从1945年起,“摆脱了一切左派的偏见”,[26] 不会再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当然也不再认为现实中的共产主义制度会比法西斯主义制度表现得更为仁慈一些。针对战后法国许多知识分子和萨特一样对苏联抱有类似的幻想——“苏联同西方协商,时间长了就能使苏联起变化,转而信奉我们的价值标准”,阿隆认为这完全是对真实情况一窍不通,他明确告诫这些知识分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三人想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苏联的极权主义“本质上以往是、将来也许仍然是要向全世界传道的,所以是要侵略全世界的。”对于阿隆来说,苏联问题是他所处时代的总问题,“如果避而不谈苏联,势必歪曲对形势的分析”。[27] 他在讨论1945年6月波茨坦会议和1945年9月巴尔干的局势时,曾两次提到在分界线上落下了“铁幕”,[28] 这无疑是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的先声。
正是从1945年开始,阿隆在诀别左翼立场的同时和萨特在《现代》杂志上进行合作,但合作关系只是持续一年多时间便终结了,他们基于巴黎高师的同学关系和在二战时期曾参与抵抗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经历,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长久合作的基础,分道扬镳完全是因为“道不同不相与谋”。1947年春,阿隆投身于法国著名的右翼报纸《费加罗报》,这标志着阿隆和萨特的彻底决裂。至1977年,他们两个人的分裂和思想冲突构成了西里奈利所说的主导了法国20世纪思想史的“30年战争”。“思想战争”围绕着一系列时代主题而展开,最主要的分歧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苏联和美国的根本不同的看法,其实质就是阿隆在1948年指出的意识形态的大决裂。
在萨特把共产主义和苏联划上等号的同时,他是把美国和世界上最邪恶敌人也划上了等号。“美国对于萨特而言是‘绝对的恶’,而对于阿隆来说则是‘相对的善’”。[29] 意识形态的大决裂在冷战体制中被实际转化为对立的两极——美国和苏联,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类根本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历史哲学。

在美苏的两强对峙中,法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边,本来是不言而喻的,按照阿隆的说法:“只有美国才具有必要的资源能提供我们奇缺的原料和机器。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友谊对我们起决定性作用。”美国的援助(在萨特的词汇中是“侵害”)“加快了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30] 但在萨特及其拥趸的一系列反美宣传中,美国庸俗的消费主义在加速法国的堕落,美国被他们描写成是一个疯狂的邪恶的国家。萨特在1953年发表于《解放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让疯狗咬了。我们要断绝与它的一切联系,否则就会轮到我们被咬而发疯。”[31] 波伏娃则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美国大兵:“七年前,我们曾经爱过他们,这些身穿土黄色军装、看上去如此和善的士兵,他们给我们带来自由。现在,他们却在保护一个为地球各个角落的独裁腐败政府——李承晚、蒋介石、佛朗哥、萨拉扎尔、巴蒂斯塔等——撑腰的国家。他们的军装,意味着我们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一种致命的威胁。”[32] 这些完全丧失理智的言论,在阿隆看来,是因为他们在伦理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是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个“世俗的宗教”蒙蔽了双眼而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
在冷战塑造的美苏对立两极的世界里,阿隆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完美无缺,相反,他认为“美国的模式是不完善的和庸俗的”,[33] 但他深信美国作为欧洲自由之子,是大西洋文明的象征,自由和民主是其成功的基础,是其扩张和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秘密所在,当然也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最强大的物质力量。而苏联制度则被阿隆定义为“意识形态制度”,共产主义作为建构其历史合法性的唯一意识形态,实质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它把意识形态看作某种教理,或一种反对宗教、否定宗教的真理,一种最高真理,党员是传教士,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最大传教士,他的讲话就是向整个苏联下达的绝对命令。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分裂的深刻理解,阿隆在《大决裂》中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大可能”。[35] 和平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美苏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苏联领导人从不承认敌对他们的行为含有合理的、正义的因素,维护共产党一党统治在国内的永久地位,和由此而来的编造外国敌视的神话,这一切决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其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性关系,指望在意识形态冲突的前提下实现欧洲的和平,那是幻想。阿隆对此明确指出:“只要俄国人民还被禁锢在愚弄谎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牢房里,只要他们还像围城中人那样忍饥挨饿,行动不得自由,那么冷战尽管有起有落,和平则仍然是毫无希望。”[36] 战争之所以也不太可能,是因为美国对西欧国家提供的军事保障和在核威慑下形成的武装力量均势,使得铁幕两边的战争机器都不敢轻易启动,核战争的后果使人类倒退到石器时代的恐怖预期,为避免战争创造了最大的约束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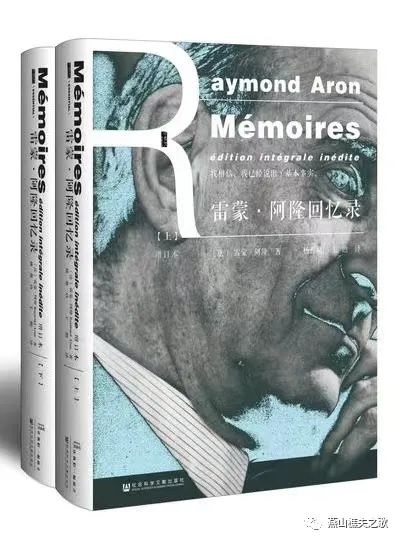
阿隆的《大决裂》似乎验证了尼采作出的“以意识形态名义进行大型战争”的预言,冷战所开创的美苏之间的对决,在法国思想界开启了阿隆与萨特长达30年的“思想战争”,以《大决裂》为时间轴心所展开的不同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是这场“思想战争”的第一回合。阿隆和萨特在这一回合中谈不上谁输谁赢,但他们各自代表的思想阵营却不是处于均势状态,阿隆不得不面对着由共产党人、左翼知识分子和中立主义者结成的神圣同盟,他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被各种势力蓄意边缘化。但是,阿隆并没有因此在他坚守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阵地上后退半步,也没有从策略上考虑向他强大的对手作出哪怕是部分妥协,他就像是一个西西弗斯式人物,因为深信历史最终将站在自己一边而不惜周而复始地努力把真理的巨石推到山顶。战后的时代以萨特命名,如果没有阿隆在场,时代的精神天平必将失衡。《大决裂》之后,阿隆在他的笔端下很快又酝酿出更为激烈的思想风暴,再一次席卷法国思想界。
本文注释:
1 [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59页。
2 参阅[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02页。
3 [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杨祖功、海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133页。
4 转引自[美]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162页。
5 参阅同上书,第162页。
6 同上书,第172页。
7 [法]梅洛-庞蒂:《人道主义与恐怖》,《梅洛·庞蒂文集》第3卷,郑琪译,张尧均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70页。
8 [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品),2017年,第92页,93页。
9 转引自[美]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217页。
10[法]让-保罗·萨特:《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文集》哲学卷),潘培庆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11转引自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56页。
12参阅同上书,第73页。
13“克拉夫琴科案”是指苏联前驻美国外交官克拉夫琴科于1944年叛逃美国,后在美国发表了《我选择了自由》一书,揭露苏联体制内各种反人类暴行。法共主办的《法兰西文学》强烈抨击此书和作者,认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造的阴谋,旨在恶毒攻击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克拉夫琴科起诉《法兰西文学》。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出庭作证时说:“这是一部带插图的反共产主义和反苏联的百科全书”,是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但法庭最后判决克拉夫琴科胜诉。有研究者认为,虽然《法兰西文学》输了这场官司,却赢得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鲁塞案”是指作家大卫·鲁塞在1949年11月12日《费加罗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救救苏联集中营里的流放者》,要求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负责前往苏联调查集中营的实际情况。这篇文章也遭到了《法兰西文学》的猛烈攻击,该报指责鲁塞“庸俗地把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搬到了苏联”,以此来篡改事实。鲁塞认为他遭到诽谤而于1950年2月起诉《法兰西文学》,次年1月赢得了这场官司。《法兰西文学》认为,虽然它在法庭上输了,却取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因为它“折断了在法国知识界抨击苏联的左翼批评家的翅膀。”相关信息资源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75-277页。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82-89页。
14[法]梅洛-庞蒂:《人道主义与恐怖》,《梅洛·庞蒂文集》第3卷,郑琪译,张尧均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03页。
15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87页。
16[法]让-保罗·萨特:《共产主义者与和平》,转引自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166页。
17转引自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129页。
18转引自[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王文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
19转引自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213页。
20[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33页。
21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88页。
22转引自同上书,第310页。
23参阅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74页。
24[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219页。
25同上书,第219页。
26同上书,第220页。
27[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221页、224页。
28参阅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182页。
29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77页。
30[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290页。
31转引自同上书,第439页。
32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278页。
33[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74页。
34参阅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90页。
35[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403页。
36同上书,第4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