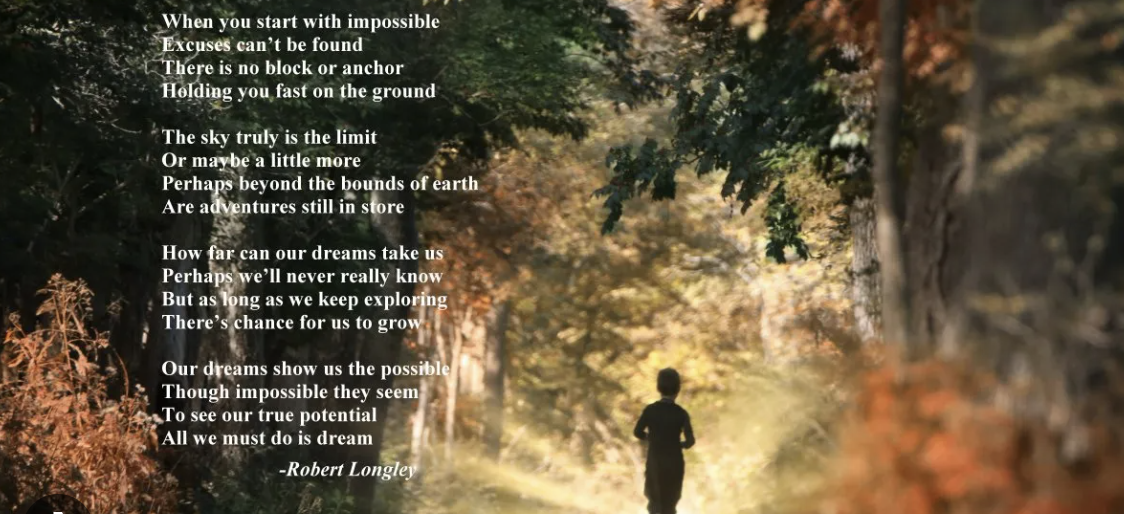
STARTING FROM THE IMPOSSIBLE
——“反抗”主题之我见
“持不同政见者”,曾是共产专制反抗者的专用称谓。这个词语的内涵,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更明确说,今天,我们反抗谁?反抗什么?
1989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历史在我们眼前背道而驰。苏联、东欧流亡者回家之日,却是我们开始流亡之时。噩梦诡谲地轮回,就在不久前,战争罪犯普京,得意洋洋地踏上中国美国和印度的红地毯。我几乎能看见,他每个脚印里,都汪着天安门广场上被坦克履带碾烂的血肉。
一九五零年代中国的政治口号“大跃进”,换一个字“大跃退”,就能完美表述冷战后的世界。当代人类精神危机,远比冷战时期严峻。意识形态话语崩溃后,“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幻象,掩盖了可怕的现实:专制极权和西方大资本悄然汇合。共产党和资本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思想控制,通过人的欲望自动完成。一个“进化论”的玩笑:发财,等于放弃精神原则。既然没有愿景,就只剩抓取眼前利益。于是,自私,玩世,利润第一,画出了一幅世界丑陋的肖像。
我的诗《一九八九年》,结尾于:“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这里,隐含着对我们自己的追问:如果天安门让我们震惊得就像第一次听说大屠杀,那么对反右、文革中无数冤死者的记忆哪儿去了?如果他们只是被忘了,谁又能保证这次的眼泪不在冲洗掉记忆,准备下一次震惊?今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邪恶“老大哥”公然结盟,民主制度沦为私欲操控的“多数游戏”,而世界对此无奈无力,连最敏感的诗歌也在对它刻意回避,麻木和失语,使我们沦为泡沫。
我们内心的茫然,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民主”的失望。原本以为当然正确的民主规则,这么容易被颠覆,甚至沦为毁灭自由的工具。“民主”成了大问号,悬在每个人头顶。但,这不就对了?民主,没有一劳永逸的固定结论,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在自我辩驳中摸索前行。于是,“持不同政见”, 必须基于对自我的追问,在追问自我中追问世界。这回到了“反抗”的本质:不仅针对外在强权,更该针对人自身的精神沦丧,因为正是每个人的精神放弃,给极权控制创造了机会。今天的反抗者,必须是“主动的他者”,以自我追问为能量,我问故我在,自觉抗拒自我的惰性,无论它有多少既得利益。
这让我想到奥威尔的《1984》,写于冷战时期(因此暴得大名),却绝非冷战宣传的工具,更是对一切极权思维方式的研究。那张蓝图,揭露出如今遍地“老大哥”想要隐藏的嘴脸。奥威尔借温斯顿的嘴,写下《1984》最可怕的结尾句“他爱老大哥”,也延伸成我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爱老大哥》。《罪恶研究》①,不在别处、远处,就在我们脚下和自己之内!无论灾难相距多远,都必然能找到人性的黑暗那个源头。这个不可能,“普普通通”又无比真实,体会、领悟它,由此理解走投无路的处境,再以超强的能量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不意味文明的崩溃,恰恰印证了自信,且成为一切现代文明的标志。
这篇短文,归结于两句话:一,“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二,Starting from the Impossible。奥威尔的大作仍在前面,它摧毁了乌托邦幻象,同时印证了人的尊严和文明的本质。
① 一首杨炼诗作的标题。
杨炼
2025年12月12日,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