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挪威作家Jon Fosse。在Fosse之前,挪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家当属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他是鲁迅很喜欢的作家,因此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坛很有影响。我没有读过Jon Fosse的作品,因此无法评价。但关于Fosse作品所使用的语言,联想到东亚语言的情况,结合我在德国与一位丹麦朋友交谈所得到的见识,我有一些想法。Fosse与易卜生都使用挪威语写作,但他们所用的语言却有很大差异。易卜生用的是“书面挪威语”(Bokmål)他的作品大多在丹麦出版,而Fosse所用的是“新挪威语”(Nynorsk),两种文字在拼写、词汇、语法上都有不小的差异。挪威人口总共只有500多万,为何会有这么大差异?
这是因为,历史上从1524年起,挪威与丹麦是一个国家,称为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到1813年,因为瑞典入侵,丹麦打了败仗,而将挪威割让给了瑞典。原先,丹麦靠近欧洲文明的核心区,而挪威是边缘,文化是从丹麦朝挪威的方向传播。因此,挪威越是大城市、越是上层社会,说的语言就越接近丹麦语,而偏远地区则说各自不同的方言。挪威被丹麦割让给瑞典以后,挪威人担心瑞典人强制用瑞典语替代自己原来的语言,萌发出挪威民族意识。但在铺开公立学校教育时,偏远地区的挪威儿童在语文课上遇到很大困难,因为他们的母语与挪威大城市里说的那种靠近丹麦语的语文差异很大。这时,挪威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既然挪威民族不是丹麦人,是否应该把语言中受到丹麦语影响的部分清除掉?
这时挪威出现了一位语言学家和作家:伊瓦尔·奥森(Ivar Aasen, 1813-1896),他刚好是一位边远地区的农夫之子。他有点像德语的奠基者格林兄弟一般,在挪威的各个偏远地区搜集民歌,调查各地的方言。他采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挪威各地方言的祖语形式进行重构(Reconstruction),他在1853年出版著作,发表了他重构的挪威语,被称作“新挪威语”(Nynorsk)。在挪威,实际上没有人实际用这种语言作口语交流,它是语言学上构想出来的挪威各方言的源头。今天,使用受到丹麦语影响的“书面挪威语”的人群约占85%,他们多集中在挪威靠近首都奥斯陆的东部接近丹麦的地区,使用“新挪威语”的占约15%,多在西部地区。Fosse用的就是“新挪威语”。
欧洲与中国、美国的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欧洲遍布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文字。在瑞士和东欧一些地区,一个人能熟练掌握三四种语言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中国有人说自己能说三四种外语常会被人认为是了不起的,然而在欧洲,大家早已司空见惯,没人会觉得你了不起。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的理性主义与世界主义对当时小邦林立的日耳曼地区产生强大压力,因此19世纪的德国人提出浪漫主义,亦即强调德意志传统的独特性。在浪漫主义朝东欧、北欧的传播过程中,各种小的族群受到刺激,发展出各种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
分析中欧、东欧的诸种“民族语言”的产生过程,基本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史诗,第二阶段是《圣经》的民族语言译本,第三阶段是民族文豪。以德国为例,三个阶段分别是《尼伯龙根之歌》、路德的《圣经》译本、歌德。对于英国来说亦有类似的演进,即《贝奥武夫》、詹姆士国王本《圣经》、莎士比亚。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演进是同步的。日本的理论家柄谷行人写过一篇论文《书写语言与民族国家》,对书写语言的创制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有很精辟的分析。
在东亚,原本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之间,汉语文言文是一种跨区域的上层阶级交流的书面语,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清末时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滔天无法用口语交流,只能通过手写文言文的方法来交流,他们笔谈的资料现在都保留下来了。
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民族国家体制向东亚传播的过程中,日本将琉球与阿伊努人整合进国家体制中,朝鲜、越南脱离了中华文化圈,废除了汉字。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书写语言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他们把《红楼梦》捧上“民族史诗”的生态位,这个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刚好出版了白话文的和合本《圣经》,而鲁迅占据了“民族文豪”的生态位。由此形成了汉语白话文的书写语言和中华民族主义的观念,相互配套。
但是,早期的重要的白话文作家,一半以上都来自于吴语区。白话文是建立在中国北方话的基础上,对南方吴、闽、粤三种方言的整合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在民国时代,白话文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一种非常矫揉造作、不自然的书写语言。因为白话文的设计不够自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因此被严重限制了。在中国有无数学者靠着研究鲁迅吃饭,但是如果把鲁迅的作品和欧洲文豪比较一下,会发现差距实在大得很。
民国的许多作家对白话文的不自然都有体会。胡适和张爱玲出身于吴语区,二人都非常关注用苏州话写成的小说《海上花传奇》,张爱玲几乎花了半生来研究、翻译《海上花传奇》。胡适对这本小说的评价就是“平淡而近自然”。胡适和鲁迅等人设计的白话文原本是想要替代文言文,但实际上并不是“我手写我口”,反而是变成了一种“新文言文”。
白话文作为“新文言文”的特质在香港体现的特别明显,香港人口说的粤语与他们的书面语在词汇、语法上都有不小的差异,香港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他们可以用粤语的音逐字朗读《人民日报》。香港人的书面语也基本是按照普通话和白话文的词汇与语法规范。20世纪后半叶香港流行文化的兴盛中,许冠杰曾经尝试用粤语土白来为流行歌曲填词,在当时很受欢迎,但却没有形成传统。后来的林夕、黄伟文的歌词又回到了官话白话文的文学传统中。
官话白话文与口语的冲突,在台湾也非常突出。因为新文化运动发生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原本的语言也与汉语北方话有很大差异。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发展出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与文学传统。在当时的台湾,有用日文写作的作家,也有人用汉字闽南语,也有人继续使用汉语文言文,台湾长老教会发明了“台语罗马字”,全部用拉丁字母书写台湾闽南语。1949年,国民党携带大批大陆精英渡台,在此过程中与台湾原本的中产阶级发生冲突。国民党在政治镇压之余,也大力销毁、禁止台语罗马字的《圣经》,要求台湾人学习“国语”,这种情形在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可以看到。
从吴、闽、粤地区口说语言与官话白话文之间的龃龉,可以看出官话白话文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绝不是天然的“我手写我口”,而是隐含着对应的政治建构。这种政治建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逻辑的延申。在1996年台湾总统公投以后,台湾的政权逐渐本土化;2008年以后,香港的本土主义思潮兴起。这些政治变动都促使我们反思“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弊端。
“五四一代”认为中国专制政治的根源在于儒家,其实问题不在于儒家,而在于“大一统”。因为儒家有不同的流派,并不是所有的儒家流派都支持秦始皇所代表的“大一统”政治传统。
如果我们把当下中国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归结到共产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政治传统是好的,是共产党破坏了美好的中国传统,这种认识不能算完全错误,但未免过于轻易了。60年代的国民党在台湾即推行这样的意识形态,但台湾人是和平演变了国民党政权以后才得到民主自由的。台湾政治的民主化与文化上的本土化是互为表里的过程。许多中国的自由派都知道要学习台湾,但理解台湾历史的深层逻辑的人不多。仅仅把台湾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与台湾人身份认同的转化,反映的是一种中华文明“转基因”的过程。中国要想民主化,不仅仅是推翻共产党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还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转基因”,把强调“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转到欧洲文明的逻辑上来。
中国有一些“皇汉”很喜欢嘲笑欧洲,他们认为欧洲的语言太多了,欧盟每天都要花巨额的成本来实现欧洲各国之间语言的翻译,如果像中国这样统一成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文字,该有多么方便?但事实上,中国这样大一统的逻辑,假使推广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说中国话,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毋宁说,是中国的大一统逻辑,和世界秩序的主流是水火不容的,最后冲撞的结果,一定是中国被碰到头破血流。
如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中那样为统一语言而骄傲自豪,但事实上越是统一、强调一致性,文化的生命力越孱弱。中国有十几亿人,但文化上的影响力比欧洲一个几百万、几千万人口的小国要差得多。如瑞典只有一千多万人,还不到上海人口的一半,但全世界的顶尖人才做梦都想得到瑞典人的承认,拿到诺贝尔奖。
事实证明,越是强调统一、一致性的文明,生态就越荒芜。像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种整齐划一的表演,我们看了以后,实在应该为这种表演所呈现出的荒芜和野蛮而感到羞愧、汗颜!
当我们看到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宪政化就是本土化,二者完全就是一回事。本土意识的萌芽与宪政化的进程是互为表里的。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就没有基石。宪政和议会制就是在各个本土集团的讨价还价中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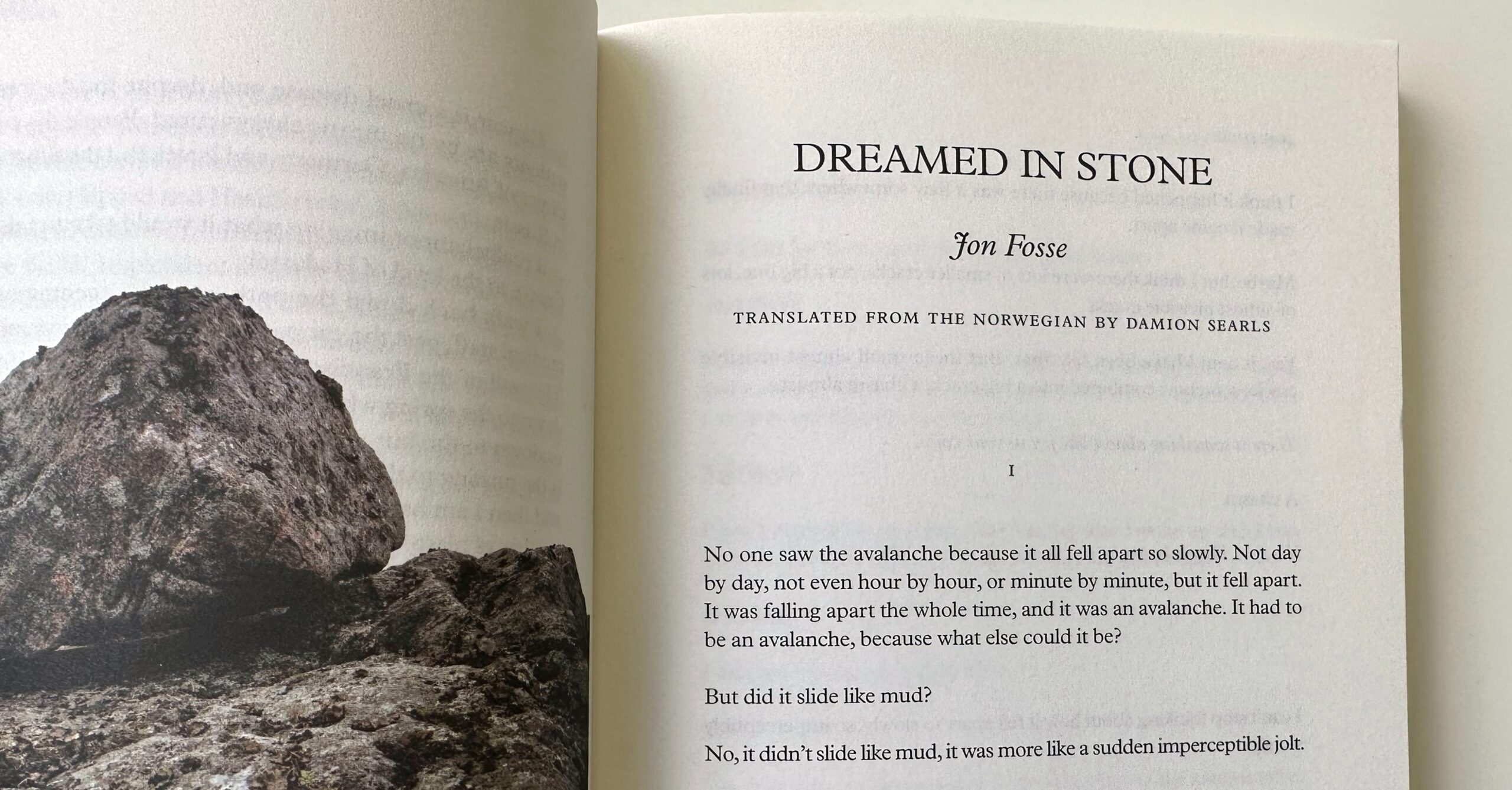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与开头所说的挪威作家Jon Fosse偏题的有点远了,但其实文学与政治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文学作为文化的核心,探索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的精神世界往往受到社会组织形式的反向建构。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往往会反映在这个社会的成员的精神状态上。而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是能够探索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精神状态的最深层,这就是德文里所说的Zeitgeist(时代精神)。社会意识的变动,与政治形势的改变,永远是齐头并进、互为表里的。而文学,就是文明的基因。
德国的文豪歌德最崇拜的就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但他却很清楚德国人无论在音乐与哲学上取得多么高的成就,在文学上就是无法出一个莎士比亚。当我们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我们常常惊叹于他取材的广泛,从雅典与罗马,到威尼斯与丹麦,莎士比亚可以说是写尽了世上的一切。莎士比亚身上所自然呈现出的国际视野与草根文化的交融,是困于欧陆一隅的德意志贵族想学也学不来的。
莎士比亚是在大英帝国的世界体系中自然成长起来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就是大英帝国世界体系的基因与DNA。人类的社会与文明在存续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动,绝没有恒久不变的东西。一个伟大的作家,绝不是把语言当成已经存在在那里的东西而拿来使用的;只有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的作家,才能成为一个顶级的作家。作家写出作品,就是在发明或改造现有的语言,也就是转变着一种文明的基因。我猜想,Jon Fosse之所以要用新的语言来写作他的作品,也正有这样的用意。

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挪威劇作家約恩·福瑟(Jon Fos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