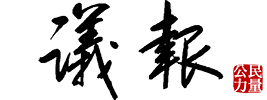一
那个女法官叫郑念,是中级法院刑庭的法官,马小龙的判决书上也有她的名字,是合议庭成员之一,但不是案件主办人。我让马翠萍拿出照片来比照,虽然十多年之后模样有些变化,但从眉眼上看,仍然能认出是同一个人。
真是太巧了。马翠萍说。
我心道,其实也说不上巧合,十七年前能从这么个小地方考到北京去读法律的女生本来就罕见,毕业后分回来,进了中级法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和马翠萍回到毓璜顶宾馆,寻思着怎么才能找到这位女法官,她可是关键知情人,通过她,或许可以了解到这个案子背后的隐秘。我在北京读在职研究生的时候,有个女同学是烟台的,或许通过她,可以找到这位郑法官。可这位女同学的电话在同学录上,这本同学录没在身边。我给老婆打电话,老婆在酒厂上班,不在家,她也没手机,正打算给小范打电话,让她到我家书橱里去找,却突然发现房间里有一本厚厚的电话簿,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隐私概念,小城市私人电话用户也不多,都印在邮电部门编发的黄页电话薄上,我不仅找到了我同学的电话,甚至也找到了郑法官的家庭电话。
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又是周末,不出意外的话,郑法官应该在家。
我拨通了电话:郑念法官吧?您好!
电话里传来一个说普通话的年轻女人的声音:哪位?
您不认识我,我是李律师,想约您见个面,有件很重要的事跟您谈一谈。我说。
律师怎么把电话打到家里来了?莫名其妙!有事去法院谈!她口气生硬起来,啪!扣上了电话。
我再次拨通这个电话,这一次我直接开门见山:郑法官,您别忙着扣电话,您的一个同学托我给您带了一件东西,这东西不方便在单位给您,所以还是见个面好!
什么同学?哪里的同学?叫什么名字?她一连三问,依然很警觉。
您最好的闺蜜,她姓漆雕,叫漆雕华。您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室友。
我尽量把字咬准。这个名字一般人读不对,会读成漆—雕华,其实漆雕是复姓,很罕见的一个姓氏,我也是在《论语·公冶长篇》见过。
郑念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柔和下来,问:在哪里见面?
我心中一喜,成功了!很显然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同学,我跟她约了半小时后在毓璜顶酒店二楼咖啡厅见面。
二
毓璜顶酒店隔着一条马路与法院家属院遥遥相对,我坐在咖啡厅靠窗户的位置上,点了两杯咖啡,吩咐服务员等客人来了再端上来。
一会儿郑念来了,她穿着米黄色的风衣,围着一条很时髦的咖啡色真丝纱巾,脸上戴着一副硕大的墨镜,身边还跟着一个穿铁灰色风衣的三十岁左右的高个男子,平头,脸庞棱角分明,眼神凌厉。看上去像是她的同事或者男友。
我站起来,说:郑法官,很抱歉,这件事只能跟您一个人谈,别人不方便在场。
郑念冷冷地:他是公安局的,我朋友。
那就更不方便了,特别是公安。我不肯让步。
郑念见我很坚持,只好示意那个人离开,那男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离开我俩,坐到一个较远的位置上,顺手取了一张报纸,装着在看,但视线一直不离我们。
这时,服务员端上了两杯咖啡,我对服务员说,给那位先生也上一杯,一起买单。
我点的是蓝山咖啡,咖啡店最昂贵的那种牙买加进口货。
郑念没喝咖啡,神态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我同学让你带了什么东西?拿出来吧。
我把装照片的一个信封递给她。她打开,看了一会儿,脸色渐渐和缓下来,声音干涩地问道:她现在哪里?让你找我什么事?
她死了,半年前死于一场车祸。我语气尽量平淡。
她猛地站起来,口气凌厉:死了?死人怎么会委托你来找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用余光看到她的那个男友也站了起来,甚至想奔过来。
我示意她看看照片背后的那几个字——去烟台,找郑姨。说道:是她儿子带过来的。
她重又坐下,示意那个男人不要过来,看着我,问:她有儿子?在哪里?
我拿出那份判决书,推给她:在招远市看守所里。他是您的案件当事人,叫马小龙,刚被判了死刑。
郑念像怕被烫着似的把判决书推给我,急急说道:这不是我的案子,主办人是庭长,我只是挂名。这事你不要找我,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我当然知道您不是主办人,不然我就直接到法院办公室去找您了。
那您为何约我在这种私人场合见面?你要知道律师约法官在私下谈案子,是违规的。
她情绪有些激动。
可您除了是法官这个身份,还是知情人呀。我正是因为您后面的这个身份才找您的呀。我解释。
不对!郑念像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惊叫道:我同学怎么可能有这么大一个儿子?你怎么能确认这个马小龙是我同学的儿子?而且阿华和她的丈夫都不姓马!
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又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是马小龙和妹妹跟父母的合影,这张照片是那个死去的女孩书包里找到的。照片上显示的时间是1986年。
我又把马翠萍收养小龙小凤姐弟俩的经过简单说了一下。
郑念看着这张照片,上面的那个母亲笑得一脸灿烂、幸福。她喃喃道:是她,阿华。
她眼圈有些红了,说:阿华和我都是八〇年入学的,是一个系的舍友。八一年我们一起在学校门口照了这张照片,不久阿华和人大的一个男生被学校劝退了,听说是他俩参加了一个犯忌的读书会,退学后他们好像去了顺义的一个山村种地去了。我还去看过他们一次,养了好多鸡鸭,种了好多果树。她和那个男生在一起同居,没户口,当然也就没领证,不过当时还没有怀孕的迹象。就算她在学校时就怀了娃娃,那这个孩子也不可能十八岁了呀,顶多十六岁呀。
我见到了火候,说:郑法官,这正是我找您的目的。你们法院怎么就能把马小龙的年龄判成十八岁?那不成了一九七九年出生的吗?那时,您的同学还在读高中,准备迎接高考呢。这不荒唐吗?
郑念看着两张照片,情绪激动,眼睛渐渐渗出泪来,我把纸巾盒推给她,她抽了一张纸轻轻按了按眼睛,平静了一会儿,抱怨道:你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怎么不去找院长?现在案子都判了,你找我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说,我昨天才接了这个案子,傍晚才在看守所见到马小龙,他跟我说你们根本没开庭,直接就判了他死刑。看守所也给我出了材料,证明马小龙所说属实。烟台中院连死刑案件都敢这么操作了?这可真是骇人听闻啊!
李律师,请你相信我,这个案子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参加庭审,也没有参与讨论过案子,都是庭长一手操办的。但是我也不能替你出什么材料,你要是想向上级法院反映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推卸的。郑念一半恳求一半解释道。
您误会了。我说:我不是想追究您什么责任,也不用您给我出材料,我只是想知道,被杀的那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你们法院出现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无意之失还是别有隐秘?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刑庭办案子都是承办人负责制,各人负责各人的案子,合议庭成员都是挂名的,只负责签个字应景儿,没有人过问别人的案子,这是规矩。您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得走了。
她站了起来,一口咖啡也没喝。看得出她已经坐不下去了。
临走的时候她看着桌子上的她和漆雕华的合影,说:这张照片我可以拿走吗?
当然,我说过了要还给您,就不会食言。我说。
她很感激地跟我握握手,说:您放心,上级法院来核实案子的时候,我会实话实说的。该我承担的责任,绝不推辞!
我送她出了咖啡厅,他的男友跟在我们后面,突然跟我说:律师朋友,这个案子水很深的,你得小心!
他显然听到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他的话是提醒还是威胁,我一时分辨不出来。
送走了郑法官,我回到房间,马翠花对我把照片还给了郑念很不理解。我解释道:那张照片证明了我的猜想,就足够了。律师不能跟法官斗心眼儿。圣人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果然,傍晚的时候,宾馆前台打来电话,说有人给我留了封信,我下楼取来,里面是好几张漆雕华在政法学院读书时的照片合影,还有在图书馆借阅图书的卡片资料和一本同学录。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许多法大同学在北京的工作单位和电话,有在新闻单位的,更多的是在司法机关的,甚至有一个在最高法院工作。
这些资料对我最终办成这个案子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
周一。法院刚上班,我就到了刑庭办公室,把上诉状和委托辩护手续送到承办法官李明亮手上。他翻看着,又把我的律师证要去仔细核查了一番,悻悻地说了句:你们律师动作好快呀,我周六才从招远回来,周一你就把上诉状送过来了。
不快不行啊,关乎一条人命呢。我说。
李明亮把律师证和辩护手续退给我,冷着脸道:你们律师的二审辩护委托书还是你自己去高院交吧,我们只收上诉状。
我接过律师证转身告辞,他在我身后又补了一句: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现在法律已经改了,上诉期是十天,不是三天了。我们自会严格执行新规定的。
我头也不回怼道:那可不一定。法律还规定这种死刑案必须公开开庭审理呢。
我能想得出,李明亮的脸色一定被我怼成了猪肝色。
不过,李明亮的最后一句话提醒了我,这种法官,什么龌龊事都能干得出来,万一他耍赖不承认收了上诉状怎么办?便又到邮局,亲自给省高级法院寄了一次上诉状和辩护委托书。
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我到了省高院,办理手续阅卷,省高院居然没有收到上诉卷宗。于是我在省高院的招待所住下来,等了七天,每天都去催问,最后立案庭的法官都急了,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烟台市中级法院:你们搞什么名堂?马小龙案子的上诉状高院早就收到了,现在人家律师都来了,你们怎么还不把卷宗送上来?
终于,又过了三天,中院的卷宗到了,我去看卷,发现里面居然有一份吕洪东律师的辩护手续。我让马翠萍向法官说明,从来没有委托这位律师当辩护人,也没见过他,不承认他的辩护人资格。
这一次高院法官很干脆,直接把这位假冒律师的手续撤了出来,换上我的,并允许我阅卷。
我在高院看了三天卷宗,发现了一大堆问题。开庭笔录、委托人手续、合议庭合议笔录、马小龙的户籍证明统统造假,这且不说,他们居然还伪造了一份马小龙的骨龄鉴定报告,认定马小龙超过了十八周岁!
我向二审法官指出,这个案子烟台中院不是无意之失,而是故意制造假案,已经丧失了公正性。如果高院发回重申的话,他们修补了程序瑕疵,还是可能再造假案。所以我申请高院给我一张调查令,我去北京调查马小龙生身父母的情况,以证明马小龙不可能生于1979年,即犯案时不足十八周岁,不应判死刑!
我把郑念法官给我的那些照片和调查线索出示给高院的主审法官看——这是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女法官——她认真看完后,补充了一句:你还得证明本案的上诉人马小龙跟这个女大学生是母子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于是我拿到了高院的调查令,第二天就到了北京,展开了艰苦地调查。
四
我在北京待了十天,调查很顺利,不仅找到了很多漆雕华的同学,让他们出具了漆雕华在北京政法学院读书的时间(1980年—1982年)证词,从而证明了马小龙不可能出生于1979年;甚至还通过她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专业教书的一个同学,找到了漆雕华当年住院生马小龙的接生医生,还找到了她和丈夫车祸后在医院救治的医生,两个医院都出具了书证,证明马小龙和马小风是她的亲生儿女。我回到省高院,呈交了证据材料,主办法官告诉我,他们到烟台提审了马小龙,调查了所谓的“开庭”情况,核实了招远看守所反映的马小龙没有离开看守所外出开庭的事实,从而认定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但是,女法官告诉我,这个案子只能发回重审,因为,一审既然没有正式开庭,省高院如果直接开庭进行二审审理,那就等于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这也是严重违法的。
可是,如果还是由烟台中院审理,烟台刑庭的法官包括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都参与了制造假案,他们能够客观公正处理这个案子吗?我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女法官爽快地说,这个问题我们高院也考虑过,本案除了程序严重违法,实体证据也有很大问题,而纠正这个问题,法院不便越俎代庖,还需要公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查清并纠正。我们已经和烟台中院做了沟通,案子发回重审后,他们会申请高院指定管辖,然后高院再指定另外一个中级法院来审理。你今天带来的证据非常重要,留下附件,原件带回去,将来负责侦办这个案子的公安机关会找你联系,你再把原件交给他们。
省高院的安排合情合理合法,我无话可说,只好先回了平度。三个月后,济南市中级法院电话通知我作为一审辩护人到法院办理辩护手续。我很纳闷,阅卷的时候问书记员,这个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侦查吗?为何公安没找我了解情况?书记员说,北京的好几个大媒体把案子曝光了,具体承办案件的烟台公检法相关人员都受到了调查,正在接受处分。你反映的情况济南公安都已经核实了,被告人马小龙只有十五岁半,还不到十六岁。开庭的时候你把原件直接呈交法庭就可以了。
一个月后,济南中院重新开庭审理马小龙杀人案,认定马小龙杀人事实清楚,但出于为妹妹复仇,受害人有重大过错,马小龙案发后能投案自首,又系未成年人,依法从轻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从死刑到七年,马翠萍大喜过望,庭审后抱着儿子泣不成声。我对自己从事律师职业又救了一条生命感到欣慰。
马小龙是我在枪口下救下的第一条人命,后来在律师生涯中又救了三个本来会判死刑的人,分别是在烟台中院、北京市二中院和深圳中院,不过他们都有罪(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两人是毒贩),只是罪不当死。
五
二000年我在北京参加首届全国律师大会,在京西宾馆跟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我们住在一个房间——聊起这些案子,这位信佛的老律师目光灼灼,打量着我说:这是你的福报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你救了四条人命!这种事,也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发生。佛祖垂怜你,把福报都给了你。我能预感到,你的余生不管遇到多少风急浪高,都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我那时不信任何宗教,对王老前辈的话并不太当真。后来在承办吉林残疾青年罗永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时,还在长春请过王海云律师帮过忙,他请我吃饭,虽然对我涉足政治性案件感到忧虑,但依然坚信我有福报在身。再后来,他的话开始应验,我多少次躲过了死亡的威胁、躲过牢狱之灾,躲过车祸和凶险的病情,躲过了小人的构陷和有司的罗网,一直活到六十岁的今天。而王海云律师,却于2011年——我出国三年后,倒在了法庭的辩护席上,正如1996年一位同行预言的一样。
或许这个世界上真得有因果报应这回事,但我始终认为,并不是我的水平有多高,有化腐朽为神奇、起死回生的本事和能耐,而是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比如,北京市二中院审理的那件运输毒品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事人利用服装夹带运输了两公斤冰毒自云南到北京,按当年运输50克冰毒判可以判死刑的规定,我的这个当事人毫无生还的机会,可是我偏偏发现了一个程序瑕疵,警察使用没有执法权的辅警询问证人(一个出租车司机),而辅警不敢写自己的名字,写了有执法权的警察的名字,可在同一时间,这个警察在讯问我的当事人。于是在法庭上我用了一句话就打掉了控方的关键证据:侦查人员不是孙悟空,他如何能于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场所讯问(询问)被告人和证人呢?这说明这两份关键证据(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要么有一份是假的,要么都是假的,就是不能同时为真!这个漏洞警察没发现,公诉人没发现,法官也没有发现,偏偏让我发现了,于是法官只好休庭。一个月后跟我电话商量,关键证据出了问题,死刑判不住了,判无期,别上诉。当事人同意了,我也同意,等于让我一句话救了一条命。
深圳中院的那个案子更富有传奇性,四个被告合伙制造了上百公斤冰毒,检察院把他们统统列为主犯,如果这个定性成立,四个人都是死刑。我的当事人是第三被告。但看他的供述和他自己涉案的卷宗,找不到过硬的理由来反驳公诉人关于四人都是主犯的定性,于是我认真阅读了第一被告的卷宗,发现了冰毒制作的配方和操作程序,这个东西公安的侦查人员是不该放到预审卷(正卷)让律师看到的,一般情况下应存在副卷中,或者抽出来只做一个简要说明附卷即可。
当公诉人在法庭上指控我的当事人制造了液态冰毒时,我找到了反驳的理由。我说,冰毒制作的核心原料是黄麻素,制作工序有七个步骤,其中除了最后一步结晶是物理反应之外,其余各步都是添加不同的试剂发生化学反应。我们知道化学反应是由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我的当事人只参与到第四步,后面的第五步、第六步如果添加A试剂就变成了冰毒,添加B试剂就变成了解毒药,这些关键步骤都由第一被告亲自掌握,亲自操作,怎么能说我的当事人制造了液态冰毒呢?
公诉人还要强辩,我直接使出杀手锏,问主审法官:可否允许我把制作冰毒的配方和具体过程在法庭上详细说明?法官敲着法槌坚决制止,威胁道:你没看到旁听席上有多少人在听吗?还有境外的记者呢!
其他辩护律师(除了第一被告的律师)都跟着鹦鹉学舌,纷纷不承认他们的当事人是主犯,最终,除了第一被告判死刑,第二被告死缓,我的当事人和第四被告都是无期,侥幸获得了一次活命的机会。
后来深圳的同行请我吃饭,问我如何会了解冰毒的制作配方和程序,我苦笑道:不过是警察疏忽,我侥幸看到了而已。
多少年后我屡屡陷入困局却最终逢凶化吉的时候,我就越发相信,我救下的这几条人命,都是命运之神对我的使用,是借我之手为我积攒福报。我能做的,正是我的老母亲当年谆谆教诲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006年末,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小城美德兰一家神学院听了半个月的神学课程。有一天黄昏,走出教堂,信步走到一个小湖边,湖里游动着白色的天鹅和野鸭,夕阳从云层中直射下来,像圣灵灌顶,直击我的头顶,使我灵光乍现,突然悟道:
生命既然是造物主赋予的,也只有造物主有权收回,尘世的任何权威——教皇、皇帝、国王或者法律和法官,都没有权力决定人的生死,任何对生命的剥夺都是对造物者主权的僭越。所以,废除死刑是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狂妄的人类对上帝权威的最终臣服!
我把这段话记在当日的笔记上。这是我接受神启的开端。
庸常如我,何其有幸,居然四次被造物主拣选,为祂做工,并因此被恩赐了丰厚的福报!
2024年1月17日 于纽约定稿
(連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