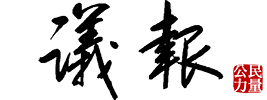春节期间,独坐在书桌前,零星的鞭炮声还在耳边炸响,空气里裹着浓浓的年味儿,我却被一股莫名的冲动攫住,像被谁点了一把火,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开个微信公众号,把那些在心底翻腾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儿倒出来,写下我的观察、困惑,甚至愤怒,试着在这喧嚣的世界里争得一点话语权。我满怀期待地注册了账号,起了个名字,埋头码字。我尽量回避乞丐式的打赏功能设置而选择付费阅读,因为此刻觉得自己像个路边摆摊的小贩,摊子上摆满了精心打磨的货品,等着有人来瞧上一眼。可现实却像一记重拳,砸得我晕头转向。我自以为有点深度的文章,点击量可怜得像个笑话,评论区空得让人心寒;那些稍带批判性的稿子,甚至连审核的关卡都过不了,也有偶然通过的时候,但很快被毙掉,平台言之凿凿地称是被读者举报和要求。
直到近日,一个朋友发来消息:“你那公众号收费观看,效益咋样?”我苦笑,回他:“哈,没人看。收费只是想筛出真正的读者。”他回了句让我心里一酸的话:“现在的东西不煽风点火的,真没人看。信息时代,东西太多,都奔着功利去了。”这话像刀子,扎得我生疼。我想起《愤怒的葡萄》里牧师凯西那句模糊的感慨,大意是“人们不再需要上帝了”。原话记不清了,但那种失落感却像潮水涌来。如今短视频席卷一切,人们似乎也不需要作家了。那些需要耐心咀嚼的文字,那些试图挖掘真相的表达,像是被时代抛弃的古董。更让我心寒的是,我花几年心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讲的是都市里的地下势力和官商勾结,上传到小说网站后,毫无悬念地被审核刷下来,屏幕上“未通过”三个字刺眼得像在嘲笑我的痴心。
可还有一件事,比审核的红线更让我心冷。不是平台,是读者,那些我以为会与我共鸣的观众。他们不仅对我的文字视而不见,甚至在面对稍有批判性的内容时,像是被触碰了逆鳞,要么自觉回避,要么跳出来攻击。我曾在公众号写过一篇关于教育资源不公的文章,措辞小心,数据扎实,以为能引发讨论。结果呢?有读者留言骂我“贩卖焦虑”,还有人说“别老盯着阴暗面,多写点正能量”。
我试着在小说里刻画一个被权力腐蚀的官员,上传片段到论坛,想听反馈,结果被喷得体无完肤,有人说“这种故事太假”,有人劝我“别写这些,容易被封”。我愣住了。这些读者,平时也会抱怨社会不公,可一旦我把这些问题赤裸裸地撕开,他们却像被踩了尾巴,急着撇清关系,甚至站在平台的立场上指责我。这让我想起福柯那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人死了。”他说的不是肉体的消亡,而是主体性的丧失——当人们被规训到与权力保持一致,自觉维护那个压迫自己的系统,人的自由意志、批判精神,就真的死了。
福柯的“人死了”指向一种深刻的现代性危机。他在《词与物》中提出,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知识、权力和话语体系建构出来的。到了现代社会,权力不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通过学校、媒体、法律等机构,渗透进人的思想,把规训内化成一种自觉的行为。人们不再需要外界的鞭子,自己就会调整姿态,迎合主流,回避异端。我的读者就是这样,他们不是故意与审查机关站在一起,而是被教育、媒体、环境潜移默化地驯化,习惯了“安全”的内容,习惯了回避尖锐。福柯的洞见在于,这种规训不是单向的压迫,而是双向的共谋——权力塑造了主体,主体也主动维护权力。
当读者面对批判性文字时,他们的不安、回避甚至攻击,正是这种共谋的体现。他们害怕任何批评性的文字触碰了那条无形的红线,害怕自己的舒适区被打破。这种自我审查的心理,远比平台的审核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批判精神的彻底萎缩,意味着人的主体性被规训成了空壳。福柯说“人死了”,不是说人不存在了,而是说,那个能思考、能反抗、能创造的“人”,已经被规训的机器碾碎,变成了顺从的螺丝钉。这让我不禁反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究竟有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从五四运动到白话文革命,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试图唤醒国民的理性与自由意识。白话文革命尤其被视为一场思想的解放,它打破了文言文的桎梏,让普通人也能通过文字表达自我、参与公共讨论。胡适、鲁迅、陈独秀们相信,语言的通俗化会让思想的火种传遍每个角落,点燃一个觉醒的民族。可百年后回看,白话文革去了什么?它革去了文言文的门槛,却没能革去思想的枷锁。
白话文让表达更普及,但也让内容更碎片、更浅薄。在短视频和算法的裹挟下,白话文的“通俗”被异化为娱乐的狂欢,严肃的思考被淹没在流量与热点的洪流里。更讽刺的是,启蒙的理想并未真正深入人心。鲁迅笔下的“看客”依然存在,只不过从街头巷尾搬到了网络论坛。面对批判性的内容,读者不是反思,而是攻击;不是对话,而是沉默。这种被规训的顺从,不正是启蒙失败的证明吗?知识分子想唤醒的“人”,似乎从未真正站立起来,反而在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器中,渐渐“死了”。我开始明白,言论自由的困境,不只是算法和审核的牢笼,还有这群被规训的读者。他们被教育、媒体、环境塑造成这样,习惯了自我审查,习惯了为权力辩护。算法是冷酷的商人,只推能抓眼球、赚流量的内容。如果文章太安静,太需要耐心,自然被埋没在短视频和热搜的洪流里。
朋友说得对,信息时代,注意力是稀缺品,读者被训练得只追逐即时快感,谁还有心思读一篇需要咀嚼的文字?而审核的红线,则是权力的铁腕。平台要生存,就得听话,得在政策的边界里小心翼翼。当小说作品触及了官商勾结的暗面,试图揭开都市光鲜下的污垢,就会连上架的机会都没有。资本和权力一拍即合,算法推流量,审核保稳定,构筑了一个看似开放、实则窒息的数字牢笼。而读者,那些我以为会与我并肩的读者,却在无意中成了帮凶,帮着权力一起,把我的声音摁进沉默的深渊。
这种无力感让我想起凯西在《愤怒的葡萄》里的挣扎。他看着人们在苦难中奔波,信仰崩塌,却依然选择行动,试图点燃希望。我呢?我还能做什么?有时候我会想,干脆放弃吧,写点爽文,拍几条抖音,蹭蹭热点,赚点流量钱。可一想到这个,我又有种被阉割的痛楚。我写作,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因为那些想法在我心里烧得我睡不着。我想写普通人的挣扎,写底层的呐喊,写被光鲜掩盖的真相,哪怕只有一个人看到,哪怕只是我自己的自言自语。
回头看这大半年的折腾,我不后悔。那些乏人问津的文章,那些被平台删除的稿子,都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叩问。言论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它是一场博弈,是无数人用笔、用心、用坚持换来的希望。我的公众号还是那个冷清的摊位,但只要我在写,就还有可能。就像姜子牙垂钓渭水,愿者上钩也好,无人上钩也罢,我守着我的笔,守着我的信念。或许有一天,有人会停下脚步,翻开我的文字,看到那个隐匿在字里行间的真实世界。忽然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语,“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不为今人赏识,但求后人能懂。
图片来自:快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