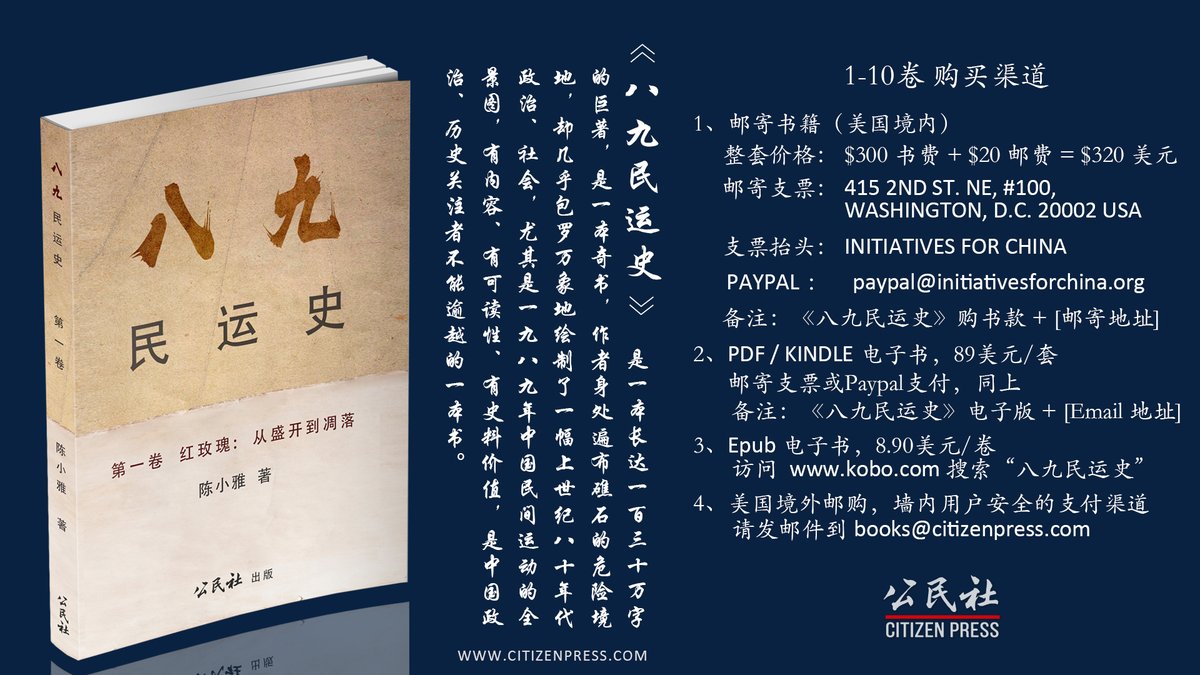
“4月15日 星期六 晴转阴 下午上班,路上遇陈维伟,政法部一位采访党政机关新闻的年青记者。他告诉我:‘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太突然了!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看两会期间登的照片,他的精神还是顶好的。虽然l2日李鹏在机场答香港记者问时,证实耀邦同志有病在医院治疗,但没有想到病情这么严重。”[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页。]
这是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的日记。但比他更早得到这个消息的却是一家外地报纸——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并破天荒地在党报还没有发布讣告前,登出了一则消息。据当事人陆一[ 陆一时任《世界经济导报》要闻部副主任。]回忆:
“1989年的4月8日,我到北京,筹备并在12日召开了我主编的《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的发行会。……会议开完,我留在北京处理后续事务,准备乘15日晚上的火车回上海。15日(周六)中午,美国大使馆的经济参赞带女朋友来本报的北办[ 即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地处北海公园东南角的大石作胡同。]吃午饭,我们的北办是一座坐落在北海边的四合院。原来午饭是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吃的,可是刚开始端菜上桌,好久没有下雨的天下起了雨。我和常驻北办的伟国[ 张伟国时任《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只能匆忙把酒菜搬到南边会议室。吃了不久,伟国就去北屋接了个电话。回来后他神情异样地告诉我,胡德平来电话,告知胡耀邦今天早上7∶40左右去世了。在座的都默默无语。”
“……我作为要闻部负责统筹工作的副主任,凭着职业的敏感马上和已经回上海的老钦[ 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打个电话通报情况。由于那天是周六、我们出报付印的日子。我在和老钦通电话时,向老钦提出应该在这一期的头版抢发一个讣告,老钦让我直接和在《解放日报》的飞飞说。于是我就打电话到《解放日报》排字房,找到飞飞,由于当时官方讣告尚未发表,我只能在电话里向他口述了这样一个讣告。” [ 陆一《4月15日,悼念同日去世的两位前辈》,载“陆一的blog的博客”。]
重大消息未按新华社统发稿发布,这是大陆新闻史上罕见的事例。但这正是当时蕴藏在新闻界的一种冲动的反映。也正因为如此,在胡耀邦去世的时间上,“导报”讣告与官方公告并不一致。
大约在此同时,胡耀邦的“小朋友”张凯,同与胡耀邦有“难兄难弟”之谊的“改革派”理论家于光远通了电话,并从电话中证实了这一消息。于光远回忆说:
“当天下午我的研究生张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听到一个传闻,说胡耀邦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相信这是真事,他怀疑会不会那些陷害胡耀邦的人造胡耀邦的谣言对他作恶毒的诅咒。我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在电话中有一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于光远《告别胡耀邦》。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2页。]
在大学,人们知道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来自午休时爱收听电台的学生。据北大作家班白梦回忆:
“4月15日的中午,我们当时正在午休。当时同屋的一个同学正在听收音机,突然他听到了哀乐,就把耳机拔掉了,我们就听到了这个消息。”
据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的杨正泉回忆,中央电台于中午2∶04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并配发了哀乐。[ 见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白梦及其室友听到的正是这则消息:
“当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本人非常热爱胡耀邦这个形象……后来就写出来那么一句话:沉痛悼念胡耀邦先生的逝世,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民主和自由事业的巨大损失。我当时就要贴到三角地去,我的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不让去,说你在北大少惹事。后来我还是去了,大概是15号中午2∶15的时候。……当时在三角地有两幅大字报,一幅是‘耀邦不朽’,一幅是‘耀邦同志,我们怀念你’。……大概往后就是我们班上一个同学贴了第四幅大字报。”[ 白梦《学运之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8页。]
张伯笠[ 张伯笠,男,1963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报告文学作家。]的回忆证实了白梦的说法:
“第一张大字报,第一首诗,第一个对联,都是作家班出的,这没错。当时,三角地是空白的。‘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这是作家班的同学写的。”[ 张伯笠《学运之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7页。据万润南《我的 1989(1)悲剧序幕》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是冰心悼念胡耀邦文章中一句自况自哀的话,但被贴到北大校园里,就具有了特别的含义。据封从德查证,冰心那篇刊载于《群言》的短文《痛悼胡耀邦同志》写于5月2日。应与作家班的标语无任何瓜葛。]
张伯笠则贴出了一首诗:
《长相思——雨夜送耀邦》
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县泪无声。
呼一更,唤一更,聒碎民心志未成,夜深望明灯……[ 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73页。]
据第一时间赶到北大的万润南回忆,第一批贴出的大字报里还有一首改编的《奉献歌》:
“把长寿奉献给小平,把短命奉献给耀邦;把捐赠奉献给邓儿,把彩电奉献给赵子。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呢?我的苦难的百姓。”[ 万润南《我的 1989(1)悲剧序幕》。]
更多的人,是从当天晚些时候的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一噩耗的。
据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周锋锁回忆,尽管在中午时分,清华三教前的广告牌上已经出现了悼念的“白色”物件,但他当时并没有注意。确切地知道耀邦去世,还是从晚上新闻中知道的。当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北大”。[ 陈小雅《周锋锁访谈录》。2018年7月10-11日。]
平时处在信息灵通地位的体改所所长陈一谘这次也不例外。此时他正在301住院:
“4月15日,我在病床上吃完晚餐。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里传来了胡耀邦病逝的消息。我惊呆了,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从1957年在第三次团代会上,他给我题字‘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到1962年他到北大物理系搞‘甄别’时说的‘千锤百炼才能成钢’;再到1971年春节我向他汇报农村情况,他鼓励我说‘青年人的雄心壮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有大出息!’他的教诲一直激励着我克服万难努力奋进。……1978年若不是他的批示,我也调不回北京。”[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61页。]
眼泪里流出的还有他的后悔:他后悔胡耀邦“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没有抽空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他最后一次当面聆听胡耀邦的教诲,是1984年9月。
而两天前,他还去看望过住在同一家医院的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听说朴方也在301[ 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4月13日晚饭后,我让护士用轮椅推着到了他的病房……朴方躺在病床上,气色不太好。他和我说:‘我已经肝腹水了,可能活不久了。’我说:‘人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你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有问题!’我担心他为康华的事情心理上受到打击,[ 当时,中央正在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下属康华公司的经济问题。]我说:‘无论外边现在说些什么,你都要看开一些。’
……他问我:‘外边到底怎么样?’我说:‘情况不乐观。’就把知道的情况说了。我最后说:‘从去年价格闯关没成功,搞治理整顿很多东西又复旧了,民众的不满在增加。赵紫阳和李鹏的施政理念又不同,事情很难办。’朴方没有说话。与开完十三大后,他主动让我给紫阳捎话,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59页。]
无巧不成书,这一天,也是后来成为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柴玲女士的生日。当时,她和丈夫还租住在北大南门外的一间11平米的平房里,过着再世俗不过的“小日子”。那一天,她的丈夫封从德给她带回了 “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柴玲回忆道:
“当我们准备好桌子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我挚爱的猫咪小不点抓了抓我的脚踝,问我讨食吃……
封在用一个小电饭锅煮面条的时候心情特别好。 他在面条里加了一些昨天剩下的肉馅和蔬菜,我们两个在树下坐在马扎上看着电饭锅里冒出了热气。
在吃晚饭的时候,封从德提到了他收到了著名教授方励之的妻子李淑贤的回信。 封给她写信询问她是否出国留学就会被看作放弃了我们的祖国。 李跟他说不用担心,一旦他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技能,回国后就能更好地报效自己的祖国。 ” [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46—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