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网络)
2021年4月26日,海内外媒体纷纷报导了中国最高检对“王岐山‘前大管家’”董宏正式逮捕的消息。一时间,继2020年10月2日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宣布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之后,董宏再一次成了被舆论热议的新闻人物。当然,关注董宏的真正原因,是对据说是他后台老板的王岐山副主席前途和命运的浓厚兴趣。

去年十一期间,北大同学给我发了一个《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宏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人民网新闻,并加评说:“抓贼的怎么也成贼了?”我看到回复说:“我知道一个董宏,是原来人大学生会主席、薄一波的秘书,是他吗?”
作为一个副部级的中央巡视员,董宏不算是什么大人物;而且即便在他那个级别的官员圈中,他的名气也并不显赫,我相信知道他的人不会很多,他的出事在国内一般民众中很难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虽然我自承记忆力特强,但也并非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就能瞬间说出他的身世传承。我之所以能脱口而出董宏,是因为今天不见经传的他,当年在北京著名高校的学生干部圈子里口口相传的名声极大——至少在我这个交游和人脉层次的学生干部圈子里名声极大。
董宏是79级人民大学党史系本科学生,属于文革后高校招生的第三批。按照当时大学学生会换届规律,他应该是81年4月开始担任人大学生会主席的。等到我上大学时,董宏已经从人大毕业,分配到了中顾委,担任薄一波的秘书。
当年对董宏毕业去了中顾委这么一个养老休闲、暮气沉沉的闲缺所在,我们都大不以为然。要知道那个年头北大、人大这些名校的学生都是天之骄子,他们的身价、光环是今天的大学生们打破脑袋也无从想象的;至于校学生会主席、副主席这种顶尖的学生,则像经过了殿试钦点,一毕业都是要直接做官的——比如文革后第一届北大学生会主席、77级经济系张玮,一毕业就被天津要走,担任天津团市委书记;比如同届北大学生会副主席、77级法律系李克强,毕业后被北大留做团委书记,仅两年后就获任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比如文革后第二届北大学生会主席、78级中文系潘维明,毕业即担任北大团委书记兼北大党委办公室主任,也是两年后即去上海担任了市委宣传部部长,等等。再往后几年,文革后第五届学生会副主席、81级中文系谭军毕业前,五、六十个来北大要人的中直单位看了档案争着相招。不过如此盛况好景,持续了并不长时间:到了82级、83级毕业,一是大学生已经僧多粥少,二是生源基本已回归应届高中毕业,三是国家开始不包分配、“双向选择”问世,以至北大学生毕业去向一落千丈。
我认识董宏,是在85年春天,通过人大学生会的朋友。虽然和董宏相识了,但我生活在北京西边的海里——未名湖,他工作在北京中心的海里——中南海,距离隔着半个北京;我活跃在青春飞扬的氛围里,他麻木在垂老残喘的环境中,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联系和往来。
然而,世事吊诡、“天意终难料”。谁也想象不到,仅仅过了半年多,我们分处的两极世界竟然一下有了交集;我们居然因为各自的公事又见了面,而且一见就连续见了四天;
这四天的见面,又竟然分别是在人大会堂东大厅、怀仁堂和人大会堂浙江厅。
1985年夏天,中国的城市改革已经进入第二年,开始有了步履维艰的迹象。一年前还热情洋溢,满怀喜悦、激情与憧憬地喊出“小平您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逐渐产生了挫败、怀疑和焦虑的心态。恰在此季的8月15号皇军投降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人。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青年群体对日本的观感迅速恶劣到了极点——要知道不到一年前随着日本三千青年访问中国,中日关系刚刚才达到最高峰值。随即,沉寂了多年的学潮遽然又起;北京尚岁月静好,西安、成都等城市8月下旬已然发生了以高校学生为主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那个年头的学生纯真、冲动又简单,远比不上89六四时候的老谋深算,既少斗争经验,又缺乏思考,也没有内部泄密,更得不到长胡子的人在背后指点,完全是凭着直觉和出自本能的蛮打猛撞——西安游行行列中打出“打倒胡耀邦”、“胡耀邦下台”、“抗议卖国政府”的横幅标语,喊着“胡耀邦是胡乱邦”的口号,因为他们没忘了去年胡耀邦和访华的中曾根康弘夫妇在中南海住所的四人家宴、听说过是胡耀邦擅自做主邀请三千个包括从没跨出过本岛的北海道农民在内的日本青年免费来中国旅游……一向以“为天下先”自我要求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自己这次已经落后,失落加焦躁,于是憋足了一口气计划在9月18号“九一八”纪念日这天去天安门搞一场大的,后来居上,争回北大的面子。这样跃跃欲试、大小字报连天、四处串联鼓噪的,上至中央政治局、下至北大党委早就侦知详细、恐慌万状。其实最要命的,还不是在9月18号大家心目中那个国耻日里打正在和日本好的蜜里调油、腻腻歪歪的党中央的脸,而是不知哪个倒霉催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把当年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日定在了9月18号大家心目中那个国耻日!说起1985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那可是非同小可:要知道中共建政至今,仅在1955年和1985年召开过两次全国代表会议,那是有不得不开的极其重大的原因——1985年这次,是邓小平急于要为想象中的“全退”提前做好人事、组织的安排与布局,实在等不及两年后的十三大——。九一八国耻日举国欢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胜利召开,本已是不伦不类,要是再让学生们在会场正对的天安门广场胡天黑地的折腾一番,这个脸可就丢的大了。那时距离六四还很遥远,共产党还很要面子、还丢不起这个人。于是,全党行动起来、书记处直接操作,想尽一切办法要提前将学生的企图扼杀于萌芽,不使当天酿成大乱。在今天做新旧比较,九斤老太的感叹、“一蟹不如一蟹”的民俚俗语,那真不是盖的:1985年的共产党简直是李世民再世、宋太祖还魂,百分之百的明君圣主:没人被抓、没人失踪、没人嫖娼,连茶都没人让你喝,有的只是采取政治学的方法、思想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情感学的方法一遍遍做工作。这样耐心细致、苦口婆心、不屈不挠、不厌其烦的唐三藏级别的工作一直做到9月18日凌晨,眼睁睁还没效果,于是党中央连夜断然决定采用物理学的方法: 9月18日当天锁上北大校门,禁止所有学生离开北大。但这一举动,也是冒了足以震动全世界的风险:北大87年历史上、北京870年岁月里,除了监狱,这种事还前所未有、闻所未闻。如果不是黔驴技穷,被逼到了墙角、快跳进了黄河,党中央绝不可能出此下策,做出这样低端行为、粗俗举动——不过也由此可见那时党的为人之良善:宁愿自残,也不去祸害学生。
万众期待的9月18日终于到来了。中午时分,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秋风舒爽,在外面世界各国媒体的注视下,几千名学生聚集在北大南门,待时而出,目的地天安门;与此同时,同样多的学生乱哄哄地汇聚在图书馆前,有人挥动校旗做引导,似是作为出外的第二梯队。下午一时许,以校长丁石孙名义播出的广播讲话一遍遍回荡在整个燕园;如此罕见绝少的举动、那种急促威严的声音,让人听了浑身一阵阵肃杀,如同动荡时刻、巨变关头、大乱将临——那一年,丁石孙的政治态度尚未鲜明,大家还不知道他即将要和蔡元培一起青史垂名、成为北大双峰,更还没有人做“丁之颂”,所以学生们对广播讲话深恶痛绝,第二天就把它和1976年4月5日晚上吴德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稿并排贴在了三角地——。在对丁石孙讲话的一片嘘声和咒骂声中,北大南门依旧大敞四开,并未像学生们已经风闻的那样铁将军把门。只是,像面对传说中“八字大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解放前的衙门一样,心怀天下却莫名一文的这几千名北大学生,个个望门而止,没一人越过大门。原来,大家事先或凭借经验推测、或听到惑众谣言、或闻知政府有意放出的风声,总之一致确信一旦出了北大校门,等着自己的就是水龙、警棍、暴打和监牢;而近在咫尺从南门外一直排到中关村十字路口的数不清的警察和警车更是无法埋头掩耳——北大学生虽然一向以难酬蹈海、我以我血的传统而自诩,但大家毕竟是来上学而不是来玩命、献身的,大家渴望取义,但年纪轻轻并不像舍生,遇到一个总逼你舍死亡生的冷血政府,谁能不怕呢?
就在众人犹疑不决、逡巡不前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持久的这样犹豫拖延、进退唯谷,极易消磨士气、怀疑自我、涣散斗志、动摇人心、滋生胆怯,也就是曹刿论战说的那样一鼓作气再竭三衰,必然导致人们的失望、挫败感和失败情绪,最后兵败如山倒,而酝酿中的巨变终至化于无形——这也是政府一方每次都挖空心思努力要促成的。但就在这时,隐藏在人群多个位置的处心积虑者开始有节奏地呼喊简单的短语:“出去、出去”、“上街、上街”!这是一种极为奏效、屡试不爽的手法:如同传染一样,有节奏呼喊的面积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几个人的呼喊很快变成了千人一致的咆哮。前些年我看过一本国内翻译出版的法国研究秘密战的书,里面讲到:在群众运动中最简短、最通俗的口号,是最有效、最鲜明、最具号召力、最有鼓动效果、最易被接受和牢记、最能激起现场情绪和冲动的口号,一句话:把长篇理论化作一句简短、重复的口号是煽动群众的不二法门——此所言不虚、诚不我欺也。
说时迟那时快,在把现场数千学生带动起来一起呼喊、调动和推高了众人的激情与躁动之后,暗中策动者们紧接着开始了第二个关键步骤:一些人跑到人群最前方并排向大门迈近,其他人在人群中、人群后发力向前推搡人群。于是迅速地,大队人流开始顺势借力向大门涌去。
我在北大那些年,观摩了不下十次大规模群体运动的临场酝酿和轰然爆发,深谙其中规律:百分之九十九的聚集者开始并无一定打算,均属胆怯、犹豫的旁观者,下一步如何举动完全取决于临机情势;于是,暗藏的策动者就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在那瞬间即逝的可能运作的时间里,操控、鼓动和推涨的技巧无一不是:开始随意乱叫、力争让无声的人群噪动起来;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呼喊同一句简短的口号,直到把全体在场者带动起来一起喊;再然后有一个人跳出人群往前一冲,大家借势就爆发了,而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与法不究从者的信念会使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至于此后能持续多久、又会引发什么结果,就只有听天由命了。我的这个经验和心得,想来可以补充进《乌合之众》一书和CIA教程中也!
回到9月18日的现场。就在被激动起来的大队人流堪堪就要来到北大南门前面的一瞬间,早已摩拳擦掌的校卫队员们按照党中央的预案、根据不知什么暗号,轰然一声,将北大南门牢牢闭合、重重落锁!
虽然早知道有此一举,但南大门真的关上的一刹那,还是大大激怒了学生和人来疯们。众人叫骂着冲向大门,用力推、拉,健壮一点的开始攀爬、翻越。大铁门来回晃动、咣咣作响。那个年头,共产党煽动学潮轻车熟路可制止学潮还手足无措,高校官方应对学潮还少有心得手法;不得不处在一线的干部们既不懂圆通滑头、也不会灵活机变,为了完成军令状或者火线表现,只知道拼命硬干、舍身蛮干,所以在场的一大批各系学生工作组、校团委和学生会干部们见此情景,干脆硬冲径上,用肉身去阻挡、拉扯、制止和搏斗,现场乱作一团。
与此同时,图书馆前广场上校学生会干部则直接扑上去抢夺闹事学生手里高举的校旗。
也是与此同时,五四操场还在如期举行一个官方正式的“北大学生纪念‘九一八事件’五十四周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大会”。这是党中央授意,为引导学生以“校内纪念九一八”替代去天安门游行示威所提供的一个出气的场合。对这种一厢情愿,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抱什么希望,所以还是把好钢用在了“关大门”这个刀刃上。不过,五四操场的集会还是分流了上千或是靠拢组织、或是少年老成、或是胆小怕事、或是新进入校但还是要凑热闹见世面的学生。大会由校方事先安排好一系列演讲人和演讲内容,内定演讲者讲完后,其他人随意上台、自由表达、不加限制。当然,那天我也是演讲者之一。
举世瞩目的1985年9月18日事件的最终结局,是当天下午没有一个学生能迈出北大校门。之前分散出校、潜伏广场的北大同学和其他大学零星前来的学生,左等右等接应不到大队人马,那时没有手机,也根本无法知道苏区情况;孤悬海外,处于强敌包围下的游击战士们,在和中央主力失去联络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高度的独立精神、灵活的革命策略、高超的斗争艺术、优良的政治素质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现场临时决定独自开展行动。他们集结成方队,绕天安门广场游行,高呼:“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进步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然后安静的散去,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样,北京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中国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中日关系没有被不和谐的声音所干扰。不过,取得这个大体圆满的成绩,并非是源自党中央的决策英明、北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广大党员积极分子的立场坚定和艰苦工作,而是由于北大南门以及门锁质量的过硬。
从1978年改革开放直到1985年9月18日,大学生群体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青眼有加、着力推崇、广泛弘扬的中国青年的“三个代表”。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游行时,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举动,更让邓小平顺意舒心、龙颜大悦,对大学生愈发丈母娘看女婿。9月18日事件一出,中共高层大为震惊、诧异莫名,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的妈宝怎么就突然成了离心离德。彼时的共产党比不了现在,对脸还看得很重;他们那时的心理,还和89年六四之后对大学生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再也懒得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而是直截了当不由分说的整肃、管制、改造和惩治的状态有万里之别;他们还像半是执着、半是强迫症的痴心汉,怎么也不能接受从前百依百顺、千娇百媚的情人美娇娘有朝一日忘恩负义、翻脸无情、移情别恋、另从他人,遂发誓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付出多少代价也在所不惜、务要挽回重来一样,无论从心理上、情感上、面子上都无法允许自己曾经的宠儿、承恩者加粉丝的大学生们无缘无故的反戈和背叛,下定决心要克服万难,做一个天大的工程,扭转乾坤、重新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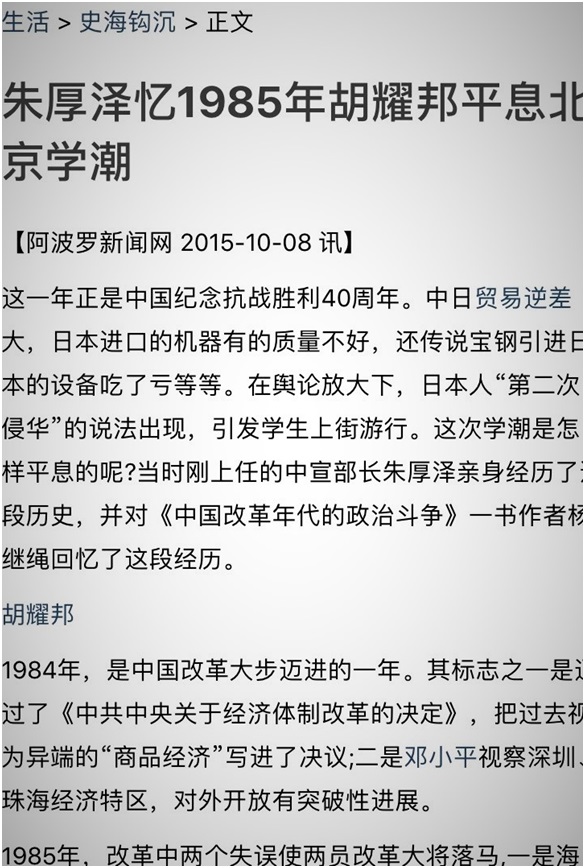
这样,从85年十一过后,中央、部委、省市,从上到下的各有关部门派出了大量领导干部深入到全国各个高校中,蹲点、摸底、调研、对话、交朋友、同吃不同住。分配到北大的,是北京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陈昊苏和团中央主管高校的书记李克强。那年晚秋和冬季的四、五个月,在树木杂色下,在金凤落叶里,在寒风瑟瑟中,在孤星和雪光间,在清晨、午后和夜晚,在北大的各个场所,每天都能遇到陈昊苏和李克强好几次,他们好像也同行同止、须臾不分。陈昊苏当时名声赫赫、又是名门之后,李克强是北大后生们的榜样和偶像,寻常见这两人颇为难得,每一见都抓住机会尽量多说几句话;没想到现如今一天能见八次,到后来再见都无话可说了,点下头赶紧走掉。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