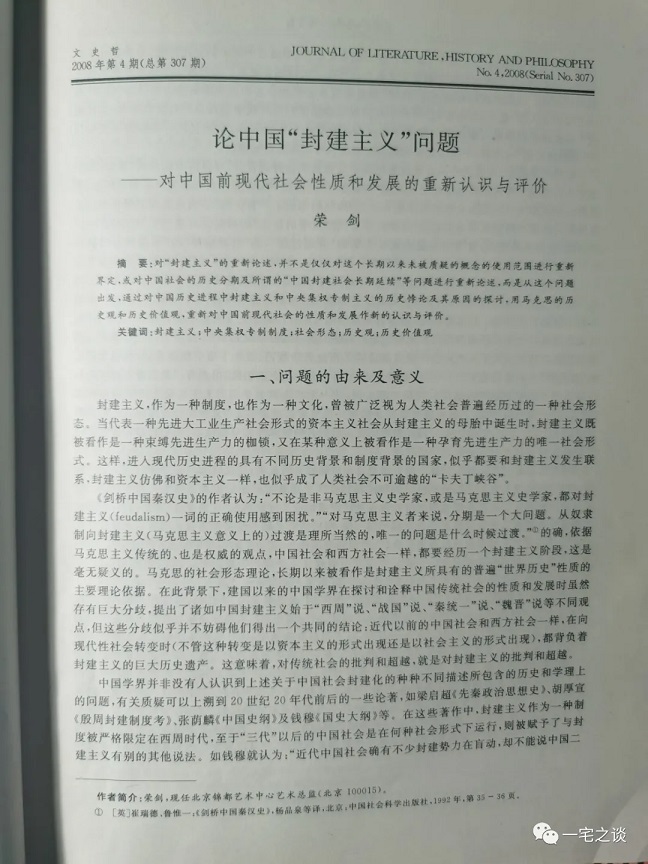来源:微信公号 一宅之谈 2021-12-15
转载: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44620
| 导读:
封建主义问题,原来是不成其为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叙事中,封建与郡县之别,周制与秦制之分,是指向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人伦秩序以及礼仪文化,几无歧义。但自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成为主导的史学叙事以来,封建主义成为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本定性,称之为封建社会,或封建专制社会。由于概念的重大误植与误读,导致了理论解释上的一系列混乱,尤其是混淆了封建与帝制的根本性区别。2002年,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出版了《封建考论》一书,该书从史观、史论、史实、史料全面考证论述封建概念及其历史边界,为彻底解决中国史学的这个最大公案奠定了无可置疑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独创性在于,从理论上对欧洲的封建化过程、中国西周封建制以及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论述作了新的梳理与表述,通过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历史悖论及其原因的探讨,重新对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性质和发展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本文发表于《文史哲》杂志2008年第四期,现分三期转发,称为“封建三论”,以呼应以前发表的“帝国三论”。 |

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一)
——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一、问题的由来及意义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也作为一种文化,曾被广泛视为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过的一种社会形态。当代表一种先进大工业生产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主义的母胎中诞生时,封建主义既被看作是一种束缚先进生产力的枷锁 ,又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一种孕育先进生产力的唯一社会形式。这样,进入现代历史进程的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制度背景的国家,似平都要和封建主义发生联系,封建主义仿佛和资本主义一样,也似乎成了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认为:“不论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都对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的正确使用感到困扰。”“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分期是一个大问题。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过渡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过渡。”1的确,依据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也是权威的观点,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都要经历一个封建主义阶段,这是毫无疑义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封建主义所具有的普遍“世界历中”性质的主要理论依据。在此背景下 ,建国以来的中国学界在探过和诠释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时虽然存有巨大分歧,提出了诸如中国封建主义始于“西周”说、“战国”说、“秦统一”说、“魏晋”说等不同观点,但这些分歧似平并不妨碍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 在向现代性社会转变时(不管这种转变是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都背负着封建主义的巨大历史遗产。这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的批判和超越,就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中国学界并非没有人认识到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封建化的种种不同描述所包含的历史和学理上的问题,有关质疑可以上溯到20 世纪20 年代前后的一些论著 如梁启超《先奏政治思相中》、胡厚宣《殷周封建制度考》、张菌麟《中国史纲》及钱穆《国史大纲》等。在这些著作中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被严格限定在西周时代,至于“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在何种社会形式下运行,则被赋予了与封建主义有别的其他说法。如钱穆就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一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2这些说法显然试图限定封建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界限而不是将其无限延伸至中国现代转型的前夜。这和所谓的封建主义“西周”说是有根本区别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经是“西周”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先秦史》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西周时代中国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但他把这一历史进程同样纳入在西周以降的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在他看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揭开了中国“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中国由此从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的封建制。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有关中国社会封建化的不同理解和诠释的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普世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当人们普遍把封建主义的“普世性”作为认定中国传统社会性质无可质疑的前提 并进而将其认定为马克思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时,他们忘记了,“普世性”的观点是属于黑格尔历史观的独特产品。黑格尔在力求超越“原始的历史”和“反省的历史”的局限性时建立了“哲学的历史”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世界历史是由理性主宰的“合理过程”,是“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世界精神”是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它的单一和统一的本性,而且这种本性必须表现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结果。黑格尔通过历史哲学的剃刀对历史的剪裁,使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再是一幅杂乱无序的图画,世界历史由此具有了它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本质,以及由低向高发展、由简单向丰富展开的特性。但遗憾的是,德国哲学深刻的背面往往就是它无可避免的片面、绝对或极端。马克思在晚年之所以拒绝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强加给他的荣誉: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就在于他清醒地看到,按照黑格尔的“普世性”方法建构起来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由此可以把握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结果。对马克思来说,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力求把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放置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但他并没有因此忽视历史发展的各种特殊性和可能性,对历史规律的逻辑叙述从来都没有被用来当作实际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社会历史观,长期以来对史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问题在于,后人在运用他的理论分析和诠释社会历史现象时往往会犯和米海洛去斯基同样的错误。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把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前的漫长时期纳入“封建主义”的框架内,并以此试图证明中国社会发展和西方社会发展的同一性,很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错误。因为马克思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意义上都没有说过东方社会(当然包括中国社会)在历中的演进中经历了封建主义阶段,更不用说东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前夜还在遭受着封时建主义梦魇的折磨。相反,马克思明确认为,东方社会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根本不存在着“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主义。
的确,马克思在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试图以此揭示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当他试图在逻辑上确立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原初地位时,并没有否认该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质和特殊的发展道路。他很清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人类社会早已灭亡的只是残留在社会古地质层的社会形态,相反,它和其他社会形态长期并存,完全在自己的轨道中独立发展;而且,它比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着更顽强的生命力,当西方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依次解体时,亚细亚社会却依然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这意味着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即“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3

在马克思的概念系统中,封建主义是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形态,是《资本论》手稿中所提到的“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的同义语,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历史。虽然马克思并未系统集中阐述封建主义的所有特征,但曾在自己的不同著述中多次提到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人身依附、大地产、等级制、政治强制等。在他看来,由于土地公有制的崩溃程度、种族和血缘的松弛程度以及个性的发展程度不同,“日耳曼所有制”不仅在历史上、也在逻辑上比“亚细亚所有制”和“古代所有制”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的母体。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4在他看来,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该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可能。
由于把封建主义看作是西方中世纪特有的社会形态,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前阶,马克思根本否认这种社会形态和东方的或古代的社会形态有什么同一性,他也反对用这种社会形态作为衡量前资本主义时期其他社会形态的唯一尺度。这些看法在马克思的晚年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等人的著作——史称“人类学笔记”时,对有关作者所谓的东方社会的“封建化”观点提出了批评。在柯瓦列夫斯基看来,东方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过程等同于西方的封建化过程。例如,他认为,印度农村公社在其解体的过程中,也达到了盛行于中世纪的日耳曼、英国和法国的那个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和中世纪的“马尔克权利”和“公社权利”一样的权利,出现了“封建的占有”。对此,马克思有过重要的评论。他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关干“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一节时,有时把“封建化过程”改写为“所谓封建化过程”;有时打上引号,以示区别。当柯瓦列夫斯基把存在于印度的“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和“荫庇制”混同于西方的封建化制度时,马克思评论道:“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5马克思在另一处还这样写道:“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6针对柯瓦列夫斯基把土耳其的统治者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军事移民区”命名为“封建的”做法,马克思认为“理由不足”。在马克思看来,在柯瓦列夫斯基的整部著作中,对所谓东方社会的封建化过程的描述,“都写的非常笨拙”。因为柯瓦列夫斯基把西方的封建主义模式完全机械地照搬到东方。马克思在摘录菲尔的著作时,对后者把东方的村社结构看作是封建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7这表明马克思坚决反对用一个统一的西方式的封建化标准来衡量东方社会.反对把人类社会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
由上可见,把中国社会的封建化问题纳入到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框架内来解决,如果不充分估计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全部或主要观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形而上学的后果。马克思不能为那些以他的名义或以他的理论所做的把历史“普世化”或“单线化”的错误承担责任。但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非封建化理论同样也不能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封建化问题的立论基础,他在批评柯瓦列夫斯基等人所作出的结论不能成为我们评判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道路的主要理论依据。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社会的封建化问题,必须彻底摆脱“普世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既要反对任何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也要反对在马克思主义面目下的各种教条式的做法。用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话来说:“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肃的理论探过 都必须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比较(同欧洲的比较),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构和发展的重大差异。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8

二、封建主义的形成及其典型形态
“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是和封建主义的历中进程与生俱来的,相反 ,当这一历中进程即将终结时,一些学者才开始注意并研究这个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已持续了一千年的社会时代的某些现象和特征。在16世纪的法国文献中,“封建”的概念首先是和中世纪特有的土地制度——“采邑”(feudum)及有关法律相联系的。随后人们进一步发现,中世纪广泛存在的“封臣制”、“采邑制”、“农奴制”及其法律体现表明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与它前后相连的两个社会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封建主义”成了旧制度的同义语,同时也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所要摧毁的对象。托克维尔(Tocquevill)的言论极具代表性:“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一切。”9 19世纪以来,封建主义成为欧洲中世纪的主要标志、“黑暗时代”的主要象征。
那么,封建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当罗马帝国的废大结构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时,在其废墟上何以“一定”建立起封建主义的城堡?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提供了纲领性的回答。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10这里,马克思精辟地看到了封建主义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谓的“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安德森在其《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对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作了更加精确的概括:“原始的方式和古代的方式的灾难性碰撞,最终产生了遍布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西方封建主义是罗马和日耳曼传统的融合的特有结果。”11美国学者汤普逊(J.W、Thompson)在其名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一书中也持相同观点。在他看来,“在日耳曼制度同罗马制度融合的过程里 无论在精神或职能方面,都有着为两种制度同时各起作用的余地。”12他把这种融合简洁地概括为:罗马贡献了财产关系,日耳曼人贡献了人身关系,它们的结合构成了封建制度的主要内容。由此,汤普逊把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由不同种族成分和不同制度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社会。
把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看作是“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融合的产物,这只是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个社会得以形成的构成要素,它们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封建主义的典型特征,因为在“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漫长融合过程中(至少约有四百年的时间),它们实际上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就“罗马因素”而言 ,在罗马帝国后期所存在的隶农制、庇护制、田庄制、大地产等这些罗马特有的财产关系并未原封不动地被日耳曼人照搬到中世纪;而所谓的“日耳曼因素”,即在蛮族的原始军事组织中保留下来的附庸制、保护制、委身制及其相应的效忠观念则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不同的社会要素的融合并由此推动一个新的社会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所决定的。他在评价日耳曼蛮人征服罗马帝国后将选择何种社会形式时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13欧洲封建主义形成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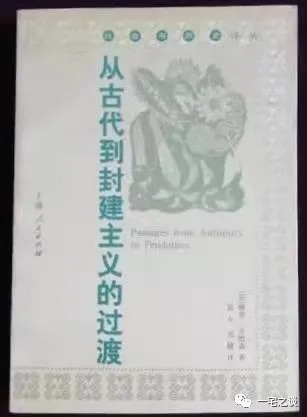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从公元 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开始计量的,但封建主义的历史并不是同时立即开始,毋宁说在8世纪法兰克宫相查里·马特实行著名的采邑改革之前,欧洲进入了封建主义的史前期。如同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封建化也需要在一个历史进程中完成它的原始积累。抛开当时繁芜复杂的历史现象,封建化的这种历史积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伴随着罗马帝国政治上的崩溃,土地的私有化导致土地的不断集中,形成大地产及其组织形态——田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无地农民——隶农对大地产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另一方面,日耳曼蛮族在不断侵入罗马帝国直至摧毁这个帝国时,它原先固有的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在罗马私有化的巨大影响之下也趋于解体,土地的分化和集中也像罗马一样开始出现,原来基于血缘和效忠观念所形成的军事组织如亲兵制逐渐被一种新的“投献”和“委身”的形式所取代,具有封建色彩的人身依断关系在日耳曼的社会组织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封建主义在这两方面所完成的历史积累最终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查里·马特在8世纪实行的采邑改革揭开了欧洲封建化的正式帷幕。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墨洛温王朝无条件赏赐贵族土地的旧制,代之以替封主服兵役为条件来分封土地,是为采邑。如果受封者不履行他所承担的义务,封主可以随时收回采邑。采邑不得世袭。马特采邑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权,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采邑制度不可逆转地演变为封臣们的世袭领地。在查里曼帝国时期,土地的封建等级所有制取代采邑制而最终成为欧洲中世纪的主要经济基础,由此构成封建主义的典型形态,即日耳曼形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把日耳曼形态或“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看作是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同义语,就如同他把“古典古代”看作是奴隶制的同义语一样。面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从来都是要求把研究对象放置在“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以至必须把现象形态上某些差别抽象掉。对封建主义的理解也是一样。虽然在日耳曼人统治的幅员广大的领土内 ,存在着众多的王国和不同的政治组织,但典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还是能够从奔腾不息的历史主流中被观察和概括出来。
首先,土地的封建等级所有制是封建主义的基础,也是它最典型的特征。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核心内容是,在承认全部土地归封建主所有的前提下,实行领主逐级分封,即国王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给教俗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又把其中的部分土地再分封给中小封建主。在上的是封主,在下的是封臣;封主和封臣之间订有契约,形成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封建的土地等级所有制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超经济强制,是封建主阶级通过政治权力对社会主要资源——土地的强行分配,并由此制约政治权力的构成和运用。
其次,在土地的等级所有制的基础上,封建庄园代替了农村的马尔克公社和自由农民的家庭组织,成为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封建领主把他分封到的土地划成庄园经营,庄园的土地分为领主直领地和农奴份地。前者由农奴耕种,产品归领主所有;后者则由农奴在剩余时间里由自已经营。从封建庄园的性质看,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实体。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权力,拥有军队,行使对农奴的政治统治。这意味着公权和私权的高度合一,由此必然导致中央王权的衰退。
第三,土地的等级所有制构成了以人身依附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在中世纪,“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 ,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制度。”14人身依附关系构成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基础。
在欧洲封建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土地等级所有制、领主庄园制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封建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或者说是封建主义“典型形态”的主要内容。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高度合一的情况,直接导致了该社会形态所特有的后果。从政治上看,公共权力被分割,王权衰弱,诸侯坐大,民族分裂;从经济上看,土地被依附于权力,人身被依附于土地,社会资源不能自由配置,土地成为“硬化的私有财产”(马克思语);从文化上看,在基督教占据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同时,为维系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契约性的文化和法律观念。

汤普逊认为,封建制度可能是中世纪人们当时所能想象到的最合适的政体,“按当时的时间、要素和条件论,在欧洲除了封建制度外,再没有其他的政府形式和社会形式可能实行的。”15法国学者卡尔迈特(Calmette)在其《封建社会》一书中明显地按马克思的方式强调了封建主义的“自然历史”性质:“封建制度不管它与先行的制度有多么大的不同,都是来自先行的制度。无论是革命,还是个人的意志都无法将其制造出来。它出现于漫长的进化道路 ,封建性属于我们称之为历史中的‘自然事件’或者‘自然事实’的范畴。”16依照两位作者的上述观点,封建主义的产生和存在对于欧洲而言是一个无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合理性和规律性总是会透过历史表象向人们显现出来。但封建主义的“自然历史”性质在多大的历史空间存在,则就必须通过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来加以判断。如果说封建主义对欧洲是一个必然的甚至是合理的过程,那是否意味着这样的过程“一定”会在所有的国家适时地发生?或者说,当其他国家在它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和欧洲封建主义相类似的历史现象时,这些现象是否也可以用“封建主义”来加以概括?进而言之,如果对上述问题予以肯定回答的话,那是否意味着封建主义作为人类必须普遍经历的社会形态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前阶?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着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封建化”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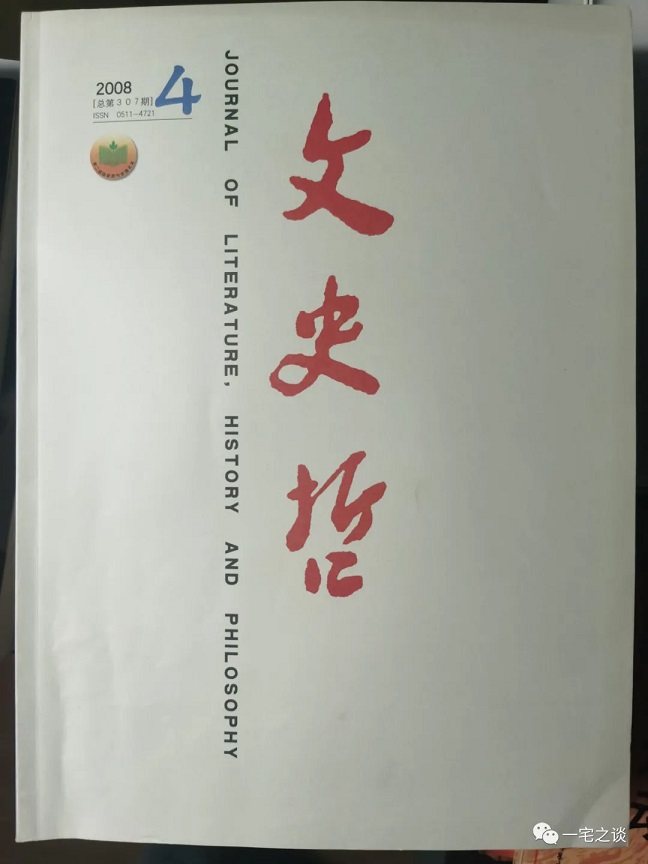
本文注释:
1 [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5-36页。
2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