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荣剑 一宅之谈 2021-12-21
| 作者导读:
封建主义是中国成文历史的开端,西周开国者周公选择“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实现“兼制天下”而不是专制天下,表明西周的政治权力体系是二元的,形成了天子之权和诸侯之权,其封建主义的性质是十分典型的。秦统一中国,是封建主义的终结,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开始,中国从此进入了帝制时代。期间出现了两次封建复辟——王莽新朝与西晋改制。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制度区别在于:封建主义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其后果必定是王国的分裂。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帝国的统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同的制度特征及其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二者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它们是无解的历史悖论。 |
副标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接上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一)
文 / 荣 剑
三、中国社会的“封建化”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的“封建化”问题对中国史学界和哲学界的主流而言 ,显然是一个不称其为问题的问题,分歧可能仅仅在于中国的封建主义起始于何时,而这些分歧似乎也并不妨碍人们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也经历了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直至晚清帝国的崩溃才宣告终结。与这种把封建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地推而广之的“普世化”做法相反,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反对把封建主义“普世化”,进而把封建主义排除在东方社会之外。以研究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而闻名的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就反对把东欧的斯拉夫的广大地区归入于西欧的历史进程,认为东欧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发展轨迹不能和它们西部的邻邦相提并论,就像不能把欧洲和欧化的国家与中国和波斯混为一谈一样。[1] 如此看来,这是否意味着封建主义只是西欧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东方社会不曾出现也无法重复的社会组织?

笔者认为,不加分析地、削足适履地把中国社会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纳入封建主义的框架内,和同样不加分析地把中国社会某个时期的历史完全排除在封建主义之外,都是犯了同样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各民族国家由于不能超越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而形成大致相同的发展模式,更无法形成统一的文化,这就为某些历史现象诸如封建主义制度涂抹上独特的地域性的色彩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的民族国家即使在完全互不联系的背景下,依然可能产生一些相同的历史现象。社会有机体在适应于外部环境和应付各种挑战的过程中,演化出相同的内部构成是完全可能的。重要的是在于,把具体的历史问题放置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予以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曾经经历了封建化的历史阶段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按照西方封建化的典型标准,也能清晰地看到封建主义实际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确切地说,封建主义是中国成文历史的开端。据司马迁的记载,传说中的黄帝开国就是从封建开始的。到了夏代,“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史记·夏本纪》),可谓开了“封建”之先河。如果说夏商二代由于缺少征而有信的文献而不能对这一时期的所谓“封建化”妄下结论的话,那么,西周的历史则能为人们提供一幅关于中国封建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画。
周人克殷,封建立国,曾被后人誉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按王国维的说法:“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他看来,殷周之际的大变革,从表象上看,是一姓一家之兴亡,但就实质而言,则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商人兄弟相及,已无封建之事。周命维新,即致力于制度创新,完成了三项重大的制度改革:“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2] 王国维对殷周之际制度变革的诠释无疑具有开创意义,但在钱穆看来,王国维似乎还未完全洞察到周人“政治上的伟大能力”,也就是说,西周的制度创新应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予以认识。

实际上,史学界对西周封建制度的起源、性质、构成和特点已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都主张“西周封建说”,而其他一些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历史学家如张荫麟、吕思勉、许倬云、黄仁宇等,则在不同时期分别对西周封建主义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至今已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西周封建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历史特点。
首先,从社会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取代文明程度较自己为高的大邑商,并选择“封建”来整合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史载武王克殷,夜不能寐,考虑的是强大的商王朝何以会崩溃,其部族联盟何以会分崩离析,而新兴的周王朝“未定天保”,又怎能避免前朝的下场呢?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武王和周公选择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这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面对幅员辽阔的领土、被征服的“殷顽民”和散布四处的各个部族邦国,西周政权根本不可能迅速建立并实行它的中央集权统治。它只能采取“分权”的管理模式,即把政治统治权分封给血缘关系最近和最具利害关系的宗族或异族成员,由他们分别治理其封地,以此确保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就有了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局面表明,西周的政治权力体系是二元的,形成了天子之权和诸侯之权。
其次,分封制下的政治权力的分割或分配,实际上也是社会主要资源——土地和人民——的再分配。所谓“受民受疆土”以及被称之为封建三要素的“赐姓”、“胙土”和“命氏”这些说法,揭示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统一性。许倬云在其《西周史》中认为,“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命氏”则包括给予国号、告诫的文辞及受封的象征。因此,西周的分封制有别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在许倬云看来,“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3这个见解是深刻的。封建主义的基本的政治单位,往往都具有宗法性、血缘性、地域性和经济性等不同特征;而正是这些不同的特征,潜藏着封建主义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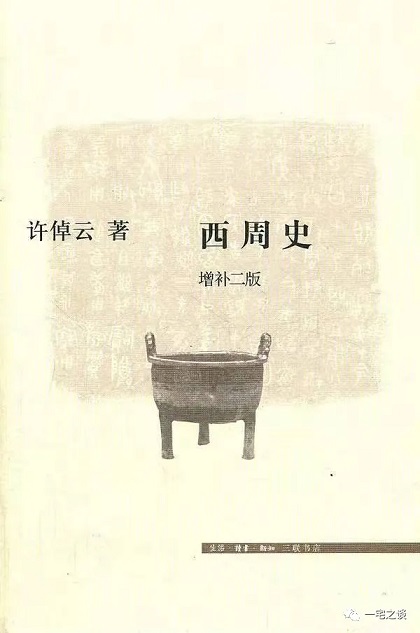
第三,周天子对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在法理上意味着他拥有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西周的土地制度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国家所有制,因为周天子是国家的人格化代表。在土地的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土地分封制,既是政治权力的下移,也是经济权利的某种让渡。诸侯在其受封的领地内行使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再次授封权,意味着土地国有制的变异,由此潜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态势。土地的逐级分封所形成的土地等级占有制, 不仅直接产生了不同的分配关系,如“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国语·晋语四》);而且也产生了土地占有者之间的等级依附关系,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左传·昭公七年》);社会的等级秩序由此形成。
第四,宗法制作为血亲关系的制度化是西周封建制的基石之一,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其核心是“亲亲”关系,是严嫡庶之辨,是嫡长子继承制,其衍生物是大宗小宗之别。嫡系谓之大宗,庶系谓之小宗。宗族内部秩序等级分明,目的在于“息争”,防止天子诸侯继统时出现僭越篡权行为,维护政权的稳定和权力更替的“合法”性。在王国维看来,宗法制下的“亲亲”关系是政治上“尊尊”关系之统,“亲亲”效及于政治,直接关系着“天位之前定”、“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严”,殷商的失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全在于不合“尊尊”之义,又无远近尊卑之分。[4] 可见,相较于分封制的分权面言,宗法制则侧重于最高主权和最高宗权的统一和集中。“亲亲”(宗统)和“尊尊”(君统)的结合,确是西周政治制度的伟大创新,是封建主义体制下统治者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卓有成效的方式。
第五,为进一步巩固分封制和宗法制,西周政治制度的奠基者周公,在摄政六年之时,开始“制礼作乐”,构建了一整套礼仪制度,制定了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行为规范,由此开创了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所谓“殷人尚鬼,周人重礼尚文”,就集中地反映了西周时代的文化倾向:“礼”,是作为宗法制的文化形态而出现的。“礼”的基本准则是“明尊卑”、“别贵贱”,是扬“天子之尊”,宣“赐命之宠”。侯外庐因此把“礼”的核心视为“别”[5],是非常精辟的概括。“礼”的各项制度化,如册封、赐命、朝觐、祭祀、巡狩、车马服章、钟鼎彝器、诗书文典、干戚乐舞等,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上下有序、贵贱有别、尊卑有等的局面。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在封建制的条件下形成天子和诸侯之间的良性的和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就权利而言,天子对诸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权”,是以诸侯服从和维护天子的最高权力及荣誉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最大限度的权力。就义务而言,为确保“天子之尊”,诸侯应对天子尽其受封时所约定的一切义务,如进贡、服役等。这表明,“礼”作为周公分邦建国的主要理念 其制度化的重要性在于把分封制下的相对分权和宗法制下的相对集权及君臣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文化”的方式结合起来,达到了孔子几乎一生都在赞叹的”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境界。
从西周“分邦建国”制度的发生、构成、内容、特征和后果来看,其封建主义的性质是十分典型的。即使按照欧洲封建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西周封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土地分封化、政治分裂化、社会等级化、人身依附化、宗族宗法化这些历史现象,完全可以视作欧洲封建主义的孪生现象,是封建主义典型形态的正常表现。史学前辈吕振羽就把西周看作是封建制时代的“典范时期”[6]。齐思和则认为,“西周时代为中国封建制度之正式开始,其政治、经济 、社会制度与西洋中古社会颇具根本相同之点。其不同者,仅枝叶问题。”[7]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和他的合作者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认为:“封建主义是否为说明周代社会政治形势特点的适当名词;如果是,它适用于将近八个世纪的整个时期,还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个时期。”“与欧洲封建主义的相似点几乎完全足以说明把这个字眼用于周代开始的四个或五个世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以后,它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只用来描述大诸侯国中不同程度地持续存在的封建状况的残余。”[8] 其实,笔者的问题也在这里:如果说西周历史的封建主义性质是无可争议的话,那么,把封建主义完全排除在东方社会的历史之外,要么就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西周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观念能够被同样用来诠释它以后的历史进程吗?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是问题更具挑战的一个方面。
四、封建化和中央集权专制的历史悖论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其根据是,从《春秋》终篇至“六国称王”的一百三十余年间,礼信尽废,不宗周王,不言氏族,不闻诗书,“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可谓“礼崩乐坏”。同一时期的王夫之则把春秋战国之交看作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叙论四》)。的确,自周平王于公元前 770年东迁洛邑开始东周历史以来,周王室日趋衰落,诸侯竞相争霸 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政治格局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社会现象。西周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个变革应当在社会转型的意义上来予以认识。
周革殷命,封邦建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转型,其实质是夏商一代的部族联盟向封建的诸侯联邦的转型,是氏族的国家形态向同封建的国家形态的过渡和演进。在西周的封建化进程中,周天子通过分封的方式向诸侯分配土地、人民和权力,形成孟子所言的“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其政治后果必然是形成天子之权和诸侯之权的二元结构,形成国中之国。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周天子在法理上、道义上和名分上虽然拥有对诸侯的最高支配权,拥有“共主”地位,但是,这种权力结构内在地包含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重新配置的所有因素及条件,包含着封建主义天然的离心倾向。
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重新配置,在春秋时代主要表现为诸侯争霸,在战国时代则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9] 其实质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彻底分化和传统政治秩序的破坏,二元的权力结构向多元的权力结构转变;另一方面,随着旧的政治权力中心——周天子共主地位——无可挽回的衰退,新的政治权力中心——强势诸侯——开始崛起。在此背景下 整合新的政治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强势诸侯在争夺霸权和土地的过程中,不再参照封建的方式来建立和维持自已的统治。土地为诸侯所垄断的事实使分邦建国几无可能,而周天子法统地位的实际丧失也使强势诸侯按传统的分封方式来分配其土地失去了法理和道义上的依据。这就为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产生并取代旧的封建的方式创造了条件,多元的权力结构由此潜藏着向新的一元的权力结构演变的可能。
春秋战国时代,通过诸侯争霸和土地兼并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政治整合方式具有其鲜明的历史特征。从经济上看,主要表现为土地制度的私有化,传统的土地国家所有及封建等级占有制趋于瓦解。史载齐国管仲于公元前685年率先采用“相地而率征”的新税法,后有晋国作“爰田”制度,进而有鲁国“初税亩”制度,至公元前498 年秦国实行“初租禾”。这些新的土地政策和制度的实行表明土地私有化已取代土地分封制而成为新的土地分配方式。到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普遍实行的按户籍身份授田制和军功赏田制,反映了土地私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从政治上看,与土地私有化相适应的是政治权力的下移和分化过程,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不仅有诸侯对周天子的非礼,更有卿大夫对诸侯的僭权。著名的如鲁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当时权力分化和整合的标志性事件。权力下移的同时,诸侯争霸中新的政治权力中心也在形成。春秋时期是轮流坐庄,霸主迭起;战国时期则是七国争雄,合纵连横。封建化的主要政治后果——分权和分裂,随着新的政治权力中心的崛起,逐渐被一种新的政治局面所取代,那就是集权和统一。这个历史使命由秦帝国完成了。
秦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是中国封建主义历史的正式终结,是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时代的开始。由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专制,既是由封建制的内在矛盾和逻辑所决定的,也是由秦所代表的新兴的政治力量迎合了社会变革时期的主流并主动进行制度创新所决定的。事实上,在战国时代曾风行一时的变法改革的浪潮中,秦起初并未站在前列。率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李悝,后实行变法改革的有赵国公仲连、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这些变法改革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共同的目标是倡导法治,鼓励耕战,举贤使能,以富兼人,推广土地私有,革除世卿世禄,实行郡县制度。其实质是废除封建,实行集权。吴起在倡言变法时就认为:“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由于变法改革直接侵害了封建贵族的根本利益,使得各国的变法改革难以顺利进行,多以失败而告终。惟秦国后来居上,一意孤行,由商鞅实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彻底的变法改革,以制度创新完成社会转型。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厉行法治,奖励军功,鼓励耕战,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开阡陌封疆,建置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按户按人口征赋,革除氏族陋俗。这些变法措施的实行,为秦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虽然,商鞅因变法被车裂而死,但他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并未由此坍塌,政未因人亡而息,国却靠制度而兴。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建主义的千年历史终于终结,中国由此进讲入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时代。
秦统一中国伊始,便面临着一个如何面对和处理封建制度的问题。以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为代表的主流意见是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理由是:“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李斯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在他看来,秦一统天下,实行郡县制,功臣诸子以国家赋税论功行赏,可长治久安,“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着秦始皇的一贯主张和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路线及实践,这是秦之所以能够战胜六国统一天下的根本保证。
秦行暴政,二世而亡,这和三代悠久的历史相比,似乎成了封建主义胜于中央集权专制的一个重要依据;“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似乎也成了秦帝国迅速崩溃的主要历史教训。刘邦底定天下后就打算吸取这个教训:“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汉书·诸侯王表》)基于这样的认识,刘邦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引入封建制,建立郡县封国并具制度,大肆封侯封爵,似乎要开创一个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和平共处彼此取长补短的崭新局面。但这样的局面根本没有出现,相反,自刘邦决定封王的那天起,不管是封“异姓王”,还是封“同姓王”,汉王朝就再没有宁静过。封建主义所代表的分裂倾向,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所代表的统一倾向,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冲突。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办法,是清除封建制度,限制直至取消诸侯的权力。用贾谊向汉文帝所上《治安策》中的话来说,“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汉书·贾谊传》)。到了景帝时期,鉴于诸侯日益坐大。已对中央集权形成致命威胁,晁错上《削藩策》,更加尖锐地提出,对诸侯的权力“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公元前154年,景帝用晁错之策开始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并在平乱后推出一系列法令和措施限制诸侯权利,规定诸侯只能衣食王国租税,无权过问王国政事,把王国的所有行政权及其官员均收归中央政权。到汉武帝时,中央政权推出了诸如“推恩令”、“左官之律”、“附益之法”等法令,继续严格执行“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政策,从制度上对苟延残喘的封建势力予以致命的清算。
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经刘邦立汉、“文景之治”,至汉武时期,中国从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基本臻于完成,借用黄仁宇的话来说,中国从此进入了帝国时期。但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冲突并未完全化解,这个历史性的悖论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体制下反复出现,似要证明封建主义仍有顽强的再生力。特别是,当封建主义演化为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念时,它对历史的影响更无法估量,它决不会轻易随制度的消失而消失。王莽的“新”政改制和西晋制度就是对这种说法的最好注脚。
王葬“新”朝,被许多人视为历史闹剧,甚至被胡适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实验。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封建主义的制度和文化在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复辟。王莽把握到了汉朝以来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土地兼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日趋扩大,流民流离失所导致社会动荡不已。为解决这些矛盾,王莽据《周礼》而实行封建制度:在土地制度上,恢复井田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在经济制度上,恢复分封制,地分九州,爵分五等;在政治制度上,恢复周代官制,设四辅三司九卿二十七大夫等。总之,在言必称周公、行必据《周礼》的氛围里,王莽对中央集权专制的庞大机体强行打入了封建主义的锲子。和王莽改制所具有的封建意义相媲美的,是西晋政权在统一中国的短暂时期里,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封建主义复辟。这次复辟的彻底性在于,西晋统治者几乎完全恢复了西周的“分邦建国”制度,分封皇族子弟二十七人为王,封侯封爵不计其数,每个封国均是拥有土地、人民、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独立国家。
和西周封建制度的最终结果一样,中国历史上这两次封建主义复辟也没有逃脱它内在的不可改变的命运,所不同的仅仅是后者存续的时间要短得多,只是历史的瞬间而已。王莽“新”朝仅维持十几年,它寄生于中央集权专制机体上的封建怪胎便被它自己的母体又重新吞噬了;而西晋封建化的可悲后果是“八王之乱”,统一的中央政权在饱尝了它自己种下的封建苦果之后,迅速分崩离析,最后演变成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社会分裂。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分分合合,王朝更迭不已,长者三二百年,短者几十春秋,其间既有汉人一统天下,也有外族入主中原;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一直被笼罩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普照之光之下。
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长期的历史悖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历史和逻辑的产物,前者赖以生存的制度是后者制度性崩溃的必然结果,而后者的存在和蔓延必定是对前者的消解。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征:
第一,从政治上看,封建主义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其后果必定是国家的分裂。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
第二,从经济上看,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前提下的封建等级占有制,土地作为社会的主要资源是通过政治权力的等级分配而进行分级配置, 土地随其占有者的身份可以世袭继承却不能买卖流转,处在硬化状态。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后者包括土地地主所有制和小农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流转。
第三,从文化上看,封建主义的文化形态是思想史上的“子学时代”(冯友兰语),文化由于政治的多元化而具有多元性的品格,诸子百家争鸣,社会思想解放。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思想史上的“经学时代”,“独尊儒术”,注经释经,思想定于一尊,形成绝对的统一的意识形态。
第四,从人的身份上看,封建主义“礼制”的核心是“别”,是社会成员的等级尊卑秩序,所有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都是预设的、固定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法制”的核心是“齐”,国家对社会成员实行编户齐民制度,所有人在法理上具有平等性,其社会地位是流动的、变化的。
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同的制度特征及其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二者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它们是无解的历史悖论。从制度而言,在农业文明时代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和配置,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显然拥有对封建主义更多的比较优势,这是它之所以取代封建主义而长期支配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根本原因。从社会发展而言,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中国整个历史进程中两个前后相继的时代,由制度变迁所决定的社会转型一经完成便不可逆转。在“路径依赖”的刚性制约之下,中国自封建主义终结之日起,就注定无法摆脱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必由之路。
本文注释:
1 参阅[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第5页。
2 王国维:《殷周制度考》,《观堂集林》卷十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453-454页。
3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50页。
4 参阅王国维:《殷周制度考》,《观堂集林》卷十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458-473页。
5 参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0、235页。
6 参阅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7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8 [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5-36页。
9 参阅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