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公众号 何处相逢
|
作者简介
王西麟(1937- ),功底最扎实、思想最深厚的中国作曲家之一。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曾遭受严酷迫害,在艰苦条件下继续进行音乐创作与研究,这也使得他的音乐逐渐形成一种深具悲剧性的风格。近年来王西麟的作品已经被中国音乐界广为接受和演出,并成为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的一部分。 王西麟还以对音乐界和中国文艺现状的直率批评而著称。本文原稿2012年在博客发表后曾引起巨大反响,网络评论高达数十万字,《黄钟》等学术期刊也刊登了相关讨论文章。现王西麟先生应本公众号邀请,对其重新修订。 |
聂耳不是作曲家(composer)
——2012年7月17日参加云南玉溪纪念聂耳百年诞辰会有感
(2020最新修订版)
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45100
2012年7月17日主办方面邀请我到云南玉溪参加纪念聂耳百年诞辰。会议快要结束时,我觉得这些话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通过那次会议,为历史说了一些全新的话。我提到的都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人云亦云的套话,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并不强求认同。
composer, 中文译为“作曲家”,这个名词很多语境下用得比较混乱,非专业词典对其也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在音乐界业内,composer的涵义是很清楚的,就是对于深刻理解经典音乐理论能够使用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的技术,并以此为基础,以立体性的交响乐思维进行创作的那些音乐家的职业称谓。composer的作品类型主要是交响曲、歌剧、室内乐中的一种或数种。与音乐创作有关的职业还有arranger编曲者,orchestrator配器者,以及写单旋律歌曲的作者,即songwriter。
songwriter中译为歌曲作者。从专业的角度而言composer和songwriter的区别是明确的,也是必须的,因为这是不同的工作范围,也是不同的评价体系。交响乐作品和歌曲作品不能够放在一起比较,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比如美国的斯蒂文柯林斯福斯特,如此著名的音乐家,就是songwriter,他既不自称composer,也不被他人称为composer。维基百科英文版开章明意的定位就是“Stephen Collins Foster known as “the father of American music”, was an American songwriter known primarily for his parlor and minstrel music.”(斯蒂文•柯林斯•福斯特被誉为美国音乐之父,是美国著名的歌曲作家,主要以客厅音乐和走唱音乐闻名。)即便贵为诺贝尔奖得主,songwriter 鲍勃•迪伦,也是既不自称composer 也不被称为composer。他的公认定位是“Bob Dylan is an American singer-songwriter, author, and visual artist who has been a major figure in popular culture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鲍勃•迪伦是一位美国歌曲作者和歌手、作家、视觉艺术家,享誉流行文化领域五十余载。)
聂耳被称为作曲家即composer,这个历史的误会已经60年了,今天还在继续。国际社会难以理解中国把写过30多首简谱歌曲、不会为自己的歌曲作钢琴伴奏的作者称为composer。聂耳没有写过交响乐作品,没有而且也还不会为自己的歌写过钢琴伴奏,也没有学过四大件等音乐理论。他是歌曲作者,是一位真正的有特殊艺术才华的歌曲作者!但不是作曲家composer。另外聂耳是用简谱写作的,由于简谱功能的不完备,composer不可能用简谱进行创作;国际上现代音乐教育中也早就摒弃了简谱,现代欧美的音乐家和音乐受众已经不知道简谱为何物。1994年我提出坚决的废止简谱,但是没有得到响应,这个话题另文讨论,此处不赘述。

我提出聂耳是不是“作曲家”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否定优秀的歌曲作品,我最为尊重的歌曲作家郑律成和沈亚威先生,还有时乐蒙先生,等等我所认识的老前辈,他们写过很多非常好的歌曲作品。讨论这个问题,既不是为了否定优秀的歌曲作者的工作,也不是为了咬文爵字,故弄玄虚, 而是因为几十年来以歌曲作品及其作者为主体的音乐评价体系,涵盖了所有的音乐创作,混淆了音乐作品的种类。对中国的音乐事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由于聂耳是国歌的原作者,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造成了只有歌曲作者的音乐地位最高这样一种怪现象,好像只有写歌曲才能算上是“作曲家”。只要一首歌被“看中”了,就升官、进京,获誉“无产阶级作曲家”,当上主席,理事,等等。却把会配器的,会写交响乐的视为为歌曲作者配器、整理、打下手的“佣人”,甚而看做资产阶级学院派而打入另册。我本人就做过许多的这样的下手活儿,汶革结束前,没有人把这样的作者称为做作曲家。这种荒唐的局面持续数十年,是对中国音乐事业的摧残,是中国交响乐发展严重滞后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认为可以用香港的办法,将这两类艺术家加以区分,分别归属于“歌词歌曲作家协会”和“作曲家协会”,两者分别进行工作,分别比较和评定。流行歌和交响乐不能混在一起,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也不要混在一起。这样也就和国际文化观念相统一了。对两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国际音乐界评价作曲家composer,是以交响曲,歌剧,及室内乐的数量和水准来衡定的。聂耳早逝,他没有写过交响乐作品,没有而且也还不会为自己的歌写过钢琴伴奏,也没有学过四大件等任何音乐理论。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发展为今天的交响乐队演奏的多声部配器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年的聂耳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的版本经过了好几位作曲家,特别是姚锦新教授的努力,由于某种原因这些都被刻意略去了。聂耳是一位业余的歌曲作者,是一位真正的有特殊艺术才华的歌曲作家,但他仍然不是作曲家composer,硬要用composer的指标来衡量他的艺术才华,对聂耳本人也是不公平的。聂耳地下有知想必也不会接受这些评价。
各国国歌的产生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能够通过音乐感染力,以非常简短的篇幅在特定场景下激起同属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共情就是优秀的国歌。并不要求各国最伟大的composer一定要做国歌,国歌的作者更不一定是该国最伟大的composer。贝多芬贵为“乐圣”,也没做过国歌;再如苏联国歌也是很优秀的歌曲,而且苏联国歌的作者、红旗歌舞团少将团长亚力山大洛夫,就是一位composer,他也有交响乐作品,国歌的多声部配器也都是他自己完成的。即便如此,也没有必要用苏联国歌去和苏俄的交响乐比较,也没有人要求苏联国歌的作者必须是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夫耶夫一般的作曲家;而代表苏联时代音乐家最高水准的是萧斯塔克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他们都没有写过国歌。
如果因为聂耳是国歌旋律的作者,就一定要尊其为最高水平的作曲家;甚至推而广之,将歌曲写得好不好作为是不是优秀作曲家的准绳,就荒唐到可笑的地步了。
西方音乐在1900年后才传入中国,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成熟的交响乐作品和作者。黄自先生1929年的交响诗《怀旧》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但极少为国人所知。所以简谱歌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音乐工具和主要的音乐现象。聂耳的歌曲基本都是在1931-1933年写出来的,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可几乎每首歌都很不错,充满灵感。我很尊重聂耳,痛惜他23岁就故世了。他创作的歌曲对民族救亡作用巨大,聂耳在中国的特殊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是卓越的,为那个时代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作品虽然是单旋律的,但是有些歌曲也表现出交响性创作思维,吸收了器乐作品的的元素,比如《大路歌》,我和朱践耳先生曾经讨论过聂耳作品的交响性,我们都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30年代学术环境是相对自由的,聂耳生活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才有了那样的创造。我看了玉溪的聂耳博物馆,很追慕那种创作的自由。但是现在的纪念聂耳的这个会议,反而全没有那样的环境了!这次会议本应该是以学术讨论为主导的,但是办成了官场式样,排名按官位大小,而且不安排自由发言。我两次要求说话都被拒绝。大多发言还是60年来的老话、套话、官话,互相抄来抄去,少有新意。更有甚者,还有与会者把聂耳和马勒相比,我才不得不说出我不同的意见了,我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承蒙主办方盛情邀请,为我付机票请我来,即便作为报答主人的盛情,我也必须讲这几句话,否则这些混乱的概念不知还要持续到何时。
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学术规律,不仅无损聂耳的卓越功绩,反而让他赢得更多的尊敬,让聂耳的英名长存。相反,如果刻意拔高,混淆不同的音乐创作类型,硬要把聂耳和马勒相比,根本是人为制造混乱,会闹出国际笑话。
和漫长的农业文明低下生产力相匹配,我国音乐的总体水平毋庸讳言也是相对落后的。政治统帅一切又把这种弱势进一步扩大,不是艺术家引领艺术前行,反而过于强调音乐喜闻乐见的宣传功能,急功近利,让艺术去迁就落后的欣赏惯性。音乐本来是提高全民文化素养根本大计,却要求成为立竿见影的政治工具。现代音乐在中国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聂耳和星海三十年代的作品,无论如何不应该当作不可触碰和不可逾越的禁区。这造成了很混乱的现象,等于人为地把聂耳树为音乐尊神,好像一首国歌就能解决中国音乐落后的全部问题。如前所述,国歌有特殊的功能,但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最高音乐水准,也不是所有音乐形式的最高典范。

出现这种局面,当然不是聂耳的责任,而且这种做法也严重曲解聂耳精神!聂耳并没有自我封神,相反他对艺术的追求令人敬佩,他深知自己专业技术的不足,为此而要去苏联学习;不仅如此,他还曾经通过贺绿汀先生恳请苏联作曲家阿夫夏洛莫夫帮助他,为他的歌曲作品配器!但是后来的某些人绝口不提聂耳的治学精神,反倒把同样努力学习外国音乐理论和技术的人统统打成“资产阶级学院派”、“单纯技术观点”大加鞑伐。1957年1962年都发生过砍掉“洋乐队”的做法,小提琴演奏家不得不半路改拉二胡,闹些“三十而立”的笑话。更加不堪回首的是,数十年来,以此为由打出了多少右派,毁了多少音乐家,整死了多少人!1957年,上海音乐学院把三位很有才能的学生(汪立三、刘施任、蒋祖馨)打成右派,他们仅仅因为批评了聂耳和星海,就被发配北大荒劳改20年。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绝不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艺术问题,更不能把政治当成打人的棍子。痛苦的历史,需要认真的反思,否则悲剧还会重演。
聂耳作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如果知道自己身后居然变成了别人手中的棍子,该是何等痛心。
这次会议使我看到云南玉溪把聂耳的历史收集的如此详尽;他们办的博物馆,使我看到聂耳30年代与许多中国电影界的代表人物合作的照片,有黎锦辉,黎锦光,任光,蔡楚生,孙瑜,费穆,金焰,王人美,黎莉莉、白虹等等前辈,真是令人感动。云南和玉溪做了很好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我向他们致敬!
不过,在作为学术著作的《聂耳全集》、《百年聂耳》等书中,以及博物馆展品的说明中,我也看到一些问题:
首先,《全集》中聂耳歌曲的钢琴伴奏,并不是聂耳作的,都是别人以后配上去的,钢琴伴奏的作者有的注明了,但是大多数没有署名,给人的感觉好像都是聂耳做的,这就造成混乱,而且侵权。如前所述《义勇军进行曲》后来立为国歌,和声和管弦乐配器作得很好,但是作者是姚锦新教授,但她从来不曾署名现在仍然没有署名。这是学术上的不严谨,而且是对姚锦新教授个人权益的不尊重。
其次,已经出版的《聂耳全集》每册2寸厚 ,上中下三大本,有6寸厚。既然叫“全集”就只能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可里面有多少是聂耳本人的音乐作品?多少是聂耳自己撰写的文章?其内容大都是纪念活动的讲话和照片,统称为“全集”,有名不符实之嫌。最好分别编辑为《聂耳作品集》和《聂耳纪念文集》。
另外,对聂耳的艺术道路的研究,我个人认为目前还非常薄弱:比如他的艺术思想是否学过或受到过俄国民族乐派的影响?他研究过哪些著名音乐作品?等等,很少有人研究。
再说一点,《聂耳音乐基金会》的功能要有新的观念。我建议:
1. 不只要仅仅唱聂耳的合唱作品,那样曲目就太少了!合唱的作品应该广泛,也可以在玉溪或昆明建立一个“聂耳音乐学校”,使学钢琴的儿童能有鼓浪屿或深圳那样多,聂耳一定会感到安慰。
2. 建立和完善昆明或玉溪的交响乐团,演出内容不作硬性规定,特别是题材自由宽泛的新作品。
3. 帮助有特殊困难的音乐家,如音乐家梁和平先生最近不幸车祸,我呼吁并请求深切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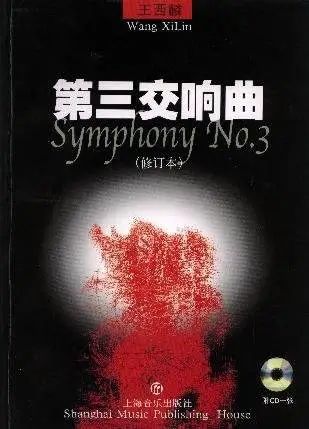
后记:再说聂耳是不是作曲家
2014年3月
我的这篇文章在博客发表以后,有网友替我把各方反馈收集起来,不完全统计就有4489个转发。文字评论达到21万多字。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可见这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
照理说,这个题目也还轮不着我来做,而是应该由音乐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专业者和音乐家协会的人来论述才对。2012年7月在云南玉溪的聂耳百年纪念会上,有一位官员(副市长?)总结发言,把聂耳和马勒相提并论,我才感到笑话越闹越大了,就算为了报答主人热心邀请,我也必须善意地纠正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错误。这才要求发言,但人家还不给机会,我只能匆匆忙忙插了了几句话。回北京后,加以整理。但这是个捅马蜂窝的题目,一定无处发表,只能放在自己的博客里。改革开放已经三四十年了,这样幼稚的错误,肯定不止我一个人看到,但人们大多不敢桶这个马蜂窝。所以我来当个拆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儿,结果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读者反馈的文字中绝大多数是赞同的。也有少数不同意见,比如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生高贺杰说我搞“哗众效果”。这就不符合事实了,读者又不傻,如果这个问题不重要,我如何“哗众”得了?
开头我就说了:本文只阐述自己的观点,引起讨论就好,不强求认同。时代毕竟前进了,我相信再不会如同1957年三位上音学子那样,因为批评“聂耳星海是音乐的最高的道路和旗帜”就被打成右派,把我也送去北大荒劳改20年。
我的目的仅仅在于区别艺术创作类别,不要以歌曲的标准覆盖一切音乐作品。在此引用留德三十年的德国汉堡音乐学院陈晓勇教授的话:“类似的概念混淆在音乐各个类别上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了,也不是没人提出过。我们看到无论是文字概念上,还是演出形式上,处处是‘大杂烩’。概念的分类与褒贬没有丝毫关系,因此各行各业间根本不必为此争风吃醋。中国在与世界接轨,想用巨资打造精神文明,行不行得通另说。国内近年来在以惊人的速度,培养出数量为世界之最的博士。建议以此作为下一个博士论题,肯定具有世界没有重复的价值。对学术的严肃态度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相反会为国人的修养的提高在国际上增光。不知为何这个本应由音乐学家做的作业,为何让站在创作一线上的作曲家王西麟先生提出来呢?!为了祖国的面子,为了中国人在世界上提高文明和修养方面地位,大家做点儿正事儿吧!”
陈晓勇教授这里说得很清楚。概念的分类与褒贬没有丝毫关系,现在却有人认为一分类就贬低了歌曲作者,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澄清文化类别。写作管弦乐作品的作曲家,也可能有很多败笔;写作歌曲的作者,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上次说过了,我很尊敬郑律成和沈亚威先生,我在歌曲作者中也有很多熟悉的好朋友。

高博士反驳我的文章说:“王先生大概认为将写作交响乐、歌剧为主的音乐创作者称为composer(作曲家),仅仅写歌曲的作者应被称为 songwriter(歌曲作者)。但事实上,composer(作曲家)的定义并非单一、固定的。以《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为例,该书关于 composition(作曲)的概念显然较为宽泛:‘创作出具有一定价值的歌曲、器乐作品、舞蹈音乐’等都被视为‘作曲’。
博士这条网评一出,立即有读者让我快快表态,意思是这下可把我“将了一军”,“可抓住了”!高博士如果是普通爱乐者,这么说话没有问题,望文生义嘛!可惜不是,他是音乐学博士。他怎么会看不出我说的是混淆两种评价体系会阻碍中国音乐创作的进步。于是只有两种可能:高博士是真糊涂或者是装糊涂。
高博士列举了《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里所说的:“创作出具有一定价值的歌曲、器乐作品、舞蹈音乐等都被视为作曲”。可是,此条是对作曲或曰创作“composition”概念的解释,你是怎么确认这一解释是对“composer”和“songwriter”的定义和区分?各种音乐辞书里定位福克斯和鲍勃是composer还是songwriter?
更何况,即使仅仅解释“composition”这个动作性名词的概念,词条中所谓“一定价值的歌曲”,首先也不是指单旋律的简谱歌曲和流行歌曲,主要是指欧洲传统的歌曲或艺术歌曲,指从文艺复兴时代的蒙特维尔第、普赛尔,到巴洛克时代的巴赫、亨德尔,包括大量的教堂合唱,又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到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直到勋伯格、巴托克和现代的(modern)和当代(contemporary)的作曲家们写作的大量的包括从古老的教会的圣诗在内的艺术歌曲作品。尤其是其中的钢琴伴奏(包括乐队伴奏和乐器伴奏)部分,甚至常常比歌声还重要得多。我所言当否,高博士可以向该辞书作者咨询。
高博士又批判我的文章说:不能“欧洲音乐中心论”,“忽视基本事实”。
我不知高博士所说的“基本事实”是指代的什么东西?不管高博士承认与否,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还果真就是当今音乐的中心和源头。否则高博士本人就不必报考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专业,直接读音乐学专业Musicology好了,当不加定语不加前缀时,“音乐学Musicology”就是研究欧洲音乐为中心的音乐,正因为承认了欧洲音乐的中心地位,你不研究欧洲为中心的音乐,就需要报考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就是欧洲以外的音乐。你就读的专业已经承认了欧洲的音乐中心地位。
中国在1900年以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音乐团体和专业音乐队伍,最有规模的音乐团体是跑码头的地方戏班子,类似吉卜赛大篷车队流浪艺人。虽然7-8世纪的唐明皇李隆基养过大型梨园,19世纪末期晚清的慈禧太后曾经收养过京剧戏班子,对京剧发展有很大推动,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的音乐发展与欧洲相比,确实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古希腊的哲学和文化对音乐的影响自不必说,之后又有数百年隶属于宗教和宫廷的悠久的传统,中国更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那样为期六百年的伟大变革和文化建设。而正是这种传统养育了欧洲的音乐,奠定了世界上以欧洲音乐为中心的格局。大约三百多年前欧洲已经有了专业的室内乐团、交响乐团、合唱团、歌剧院,所以不止中国,全世界都承认“欧洲音乐中心论”。也不止音乐如此,科学、技术、教育等等领域,也是欧洲中心论。正如高博士的读的博士学位,也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清末1906年袁世凯废除了中国千年传统的私塾科举教育制度,照搬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为什么高先生不反对“欧洲教育体制中心论”,不去读私塾考科举,中个进士行走翰林院?
什么是聂耳的优秀传统?什么是真正的聂耳精神?今天纪念聂耳到底纪念什么?
我认为聂耳有是非分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叛逆精神,在民族危急的救亡关头,他反对不抵抗主义,反对纸醉金迷的社会风气,在 《大路歌》中他为下层受压迫的工农群众的贫困和不平等而呐喊,在《开路先锋》中他呼唤他们的新的历史使命。今天在权力和金钱双重绞杀下的文化艺术还要不要发挥像聂耳那样的社会批判精神,挺身而抨击和批评权贵们的腐败、专制和独才?还要不要像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那样的去为承受不公的弱势群体的痛苦而呐喊?还要不要像《毕业歌》那样的呼唤青年同学们勇敢去承担改造社会的使命?60年来聂耳早已经被异化成为维护当权者的招牌和象征;60年来聂耳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叛逆精神早就被彻底抛弃;60年来聂耳的旗帜早已被别有用心者偷换;把历史的批判者异化为权力的卫道者。有些人把艺术作为歌工颂德、粉饰泰平、掩盖黑暗、弄虚作假、欺骗民众的御用工具,而且不惜斥巨资包装,搞得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真正的聂耳精神早就被轮番绞杀而不复存在,令人痛心。
聂耳生活的时代,虽有诸多弊端,但还没有统一的文艺审查制度,创作是自由的,他在短短三年时间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歌曲,决定性的原因就是当时有自由的创作环境。这个问题是纪念聂耳六十年来从来没有涉及的。这次在玉溪我看了当地兴建的聂耳博物馆的展品,给我深刻印象的是,30年代初期的上海有非常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尤其是电影事业,高度自由繁荣。当时的上海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导演、演员、编剧和音乐工作者。许多被我们在50年代讥讽和批判为黄色文化的人物,如王人美、周璇等都是一些很天真的小姑娘。当时最有贡献的歌曲作者任光、张曙、张寒晖、刘雪庵、贺绿汀等前辈,那种文化艺术创作环境,他们的艺术天分才得以充分发挥, 出现空前繁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如果聂耳留在云南而没有到上海,没有同行交流,没有开放的国际大都会的氛围,没有欧风美雨的沐浴,或者也有广电局中宣部的种种审查,还会有聂耳现象吗?这些因素的综合,是聂耳创作力爆发的原因。所以今天纪念聂耳,首先应该创造这样的自由创作的土壤。这是我们之所以要纪念聂耳的最重要的一条,但是却早被忘记得一干二净。就说这次会议,我看到的全是官本位观念,没有一点自由讨论的空气,发言按来宾官位排次序(据说秘书功课里专门有一课是要搞清楚官员级别的大小,排好座次,一点不能出错),所以我这样的平民在会议结束前两次要求发言都排不上队。我提出的这些意见,哪个媒体能发表?这当然不是玉溪市云南省的问题。

还有,从 50年代到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研究聂耳艺术成就的论著,都在研究聂耳的词曲结合,旋律,节奏等方面的技术,而没有涉及聂耳从欧洲古典音乐里吸收了哪些营养。我发现聂耳的30多首歌,虽然每首都是简谱单声部“赤膊调子”,但是若干作品的确有丰富的多声部的立体思维,比如《大路歌》的沉重有力,有明显的交响乐式的立体思维。《新女性》是4-5首合为一组的歌曲,但是几乎每首都有明显的不同形象的节奏音型背景的多声部因素。这也就给50年代为它们做钢琴伴奏和管弦乐队伴奏,预置了很大的艺术空间。这里要特别指出黎英海先生作的多首歌曲的钢琴伴奏,姚锦新先生做的国歌配器,今天看仍然是非常优秀的。可惜大多不被署名。从聂耳歌曲作品的上述特点分析,聂耳是喜欢古典音乐的,受过古典交响乐的影响,很重视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艺术技巧。但是见不到没这方面的资料,看来音乐学家历来也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以上都是我认为学习聂耳的精神的重要内核。而六十年来的谬误,莫过于把聂耳封神。如上文提及汪立三,刘施任,蒋祖馨三位,因发表了对聂耳星海的作品的艺术评论文章,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年,毁了一生。同时聂耳也就成为一些人的政治金饭碗,控制和把持了中国音乐事业的命脉和最高权力。把萧友梅、黄自和上海音乐学院打成资产阶级学院派,黄自的四大门生的刘雪庵,陈天鹤,也遭冷遇,陈早逝前也受尽屈辱,刘也被打成右派和黄色音乐代表,受尽迫害。1954年批贺绿汀的技术论,1957年要把贺绿汀也打成右派,幸得陈毅元帅阻止,结果陈歌辛(梁祝作者之一陈钢之父)却被用来顶替,打成右派,几年后死在劳改营,何其荒唐啊。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我们又目睹了对钱仁康先生的批判。这股可怕而强大的政治力量一直推动到“汶革”中,把一切西欧音乐统统斥责为“封、资、修”和“大、洋、古”。贺绿汀也被关押7年(我看了他的纪录片,一个可敬的艺术家,活过来了,女儿却自杀了),上音教授被迫自杀和死去16位(有资料说17位)。《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也被迫害,死于狱中。这一切悲剧如聂耳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
更可笑的是,数十年来,人为地把聂耳作品封为无产阶级音乐,似乎只能和法国大革命的《马赛曲》,和巴黎公社的《国际歌》扯上关系。现在开放了,要和国际接轨了,就又把聂耳改换门庭,和昔日划为“资产阶级作曲家”的马勒相提并论。把聂耳当作变形金刚,他们不怕闹笑话,一切看需要!
以《再说聂耳不是作曲家》为题的这篇《后记》,主要是针对前文发表后引发的不同意见的商榷;也强调了前文的重点、补充了前文的内容。
现在,应公众号“何处相逢”的邀请,做了文字修订,再次刊出。欢迎讨论,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