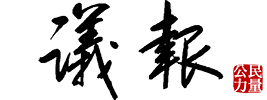中国时间(节选)
来源:格兰塔(Granta)2024年11月7日
作者:托马斯·米尼(Thomas Meaney)
译者:荔心

托马斯·米尼是《格兰塔》的编辑。他曾为《纽约客》和《哈珀斯》杂志报道,并定期为《伦敦书评》撰稿。2022年,他获得了罗伯特·B·西尔弗斯新闻奖(Robert B. Silvers Prize for Journalism)。
1
今年,我回到了一个我不再认识的北京。它不再是我80年代孩童时期第一次瞥见的那个首都,那时候,总有穿着单薄外衣的男人站在寒风里抽烟,潮水似的自行车随时要把我卷走。它不再是90年代的那个北京,那时天安门广场的扩音器里放着Kenny G的爵士乐。它也不再是胡锦涛时代的北京,那时的三里屯总是有喝到不省人事的年轻人,酒店的宴会厅里有西方学者开的法治研讨会。这座城市的旧模样似乎被抹除了,特斯拉和比亚迪的嗡鸣替代了安着挡风被的摩托轰鸣声。这次,当我走近人民大会堂时,一名警卫朝我笑了笑,好像在问:你还要来这里做什么呢?
我和北京作家陈思安坐在她的雪弗兰里,在三环路上,她跟我讲了最近中国文学面临的新问题:“传统的出版平台已经失效了,一些深入的媒体也被关停了……真正的读者已经不多了。” 今年早些时候,她的一部戏剧未能通过审批,剧院推测是因为剧情涉及疫情元素。“这像是个游戏,他们永远不会明确告诉你什么是禁忌,但你总会摸清楚这条线在哪里。” 她说:“最初我们在疫情期间做得很好,现在又要表现得像疫情从未发生过一样。” 我们在路边停下,买了瓶豆汁。我问她为什么留在北京,而不去接受海外的邀请。“用中文写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这里的一切好与坏,我的艺术就是这样了。”
曾经某时,当中国作家被问及外国文学时,会对福克纳赞扬几句。今年,我在北京与作家张悦然和双雪涛吃了顿晚饭,无法不切实地感受到中国文学界与国际文学潮流的紧密连接。他们非常熟悉地谈起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约翰·契弗、莎莉·鲁尼、本·勒纳、哈维尔·马里亚斯和J.M.库切。张悦然在本刊出版的故事《Speedwell》也受了波拉尼奥的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学消费常常通过手机实现,读者们在豆瓣上讨论作品,网络小说也以惊人的速度连载着。这个文学世界同时显得无比广阔又无比狭小。聊天时,张悦然几乎可以在微信上瞬间联系我提到的每一位中国作家,并为我提供了我仍需阅读的作家名单。
中国虚构文学最显著的发展来自东北。东北作家雪涛告诉我他最初爱上写作就是为了捕捉那些被家乡沈阳的工业衰退抛弃的人们。他特别钟情于失败者,某种程度上,这些失败者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核心。这些作品里充满了落榜生、倔强的革命者、心灰意冷的官僚、羞愧的丈夫、孤寂的女人、倒霉的混子、伤感的帮工和一事无成的普通人。从鲁迅笔下顽强生存的游民阿Q,到钱钟书笔下拿着假文凭的方鸿渐,再到余华的打老婆、赌到身无分文的福贵,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刻画着与主流影视中意气风发的英雄截然相反的形象。中文小说人物充满了愤恨,他们用这门语言复仇,用自己毁灭性的对话把它推倒再造。他们讽刺敌人的同时也讽刺自己,淡漠而凄寂地承认着,共同的挫败就是世界运行的方式。
2
如果有哪个国家是由文学作家创造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1911年的大革命,清朝崩塌,中华民国建国后,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决定,这个国家的文化需要经历彻底的变革。他们相信,过度依赖抽象宪法和空洞宣言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沉没,这些空话没能深入到平常百姓的生活里。围绕着《新青年》杂志,一群年轻的批评家提出了一系列当时看似无关紧要的要求:使用白话文、妇女权利、重新审视儒家思想、消除迷信、推崇科学。在小说和诗歌中,这些作家们建构了一个未来——农民们可以阅读、阶级可以重塑,父权大家长和地主被推翻。几年后,许多相似的变革真的发生了。
即使是斯大林熬夜亲自修改诗歌的苏联,也无法如此集中地推动文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学者,包括《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图书管理员李大钊,和上海小说家茅盾。
毛泽东本人也是位不错的诗人,他宣称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应该为人民服务。中国内战期间,他在延安的著名演讲里提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然而随着40年代文学风格的简洁化,政治气候也收紧了中国文学的创作空间。张爱玲这样有才华的作家离开了中国,而被称作“中国伊夫林·沃”的钱钟书被安排编辑毛泽东文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成了清洁工。随着识字人口的大幅提升,西方文学愈发一本难求。1949年至1966年间,每年仅出版八本小说,这一数字在1966年至1976年间进一步减少。中国成了仅推崇一本油印小册子的国家,而那本小册子就是毛泽东的小红书。
70年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市场的逐步开放也为外国文学开了口子。那个时期的中国小说里,作家们反复描写着获取这些新鲜文字的激动。单薄廉价的盗版外文书从中国印刷厂里涌出来,北京的地摊铺满了这些书。在1985年的《树王》中,阿城讽刺了这一“文学发现”热潮:下乡知青一路上拖着一箱珍贵的书籍,然而箱子里装的竟是他出于情感原因保留的毛主席全集。
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后,邓小平没有立马尝试抵挡70年代末“伤痕文学”的兴起。这一文学运动得名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该小说一夜之间写成,被张贴在复旦大学的一扇门上。她讲述了一个年轻女性在文革中与她的小资产阶级母亲决裂,离家九年,平反后回家发现母亲已经去世的故事。林培瑞等西方评论家表示,伤痕文学对极端毛泽东主义的批判力度还不够,除了台湾作家陈若曦这位个例。然而,新一代中国作家并不热衷于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西方自由主义要求他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与当年的毛主义对“纯洁性”的追求过于相似。伤痕文学不断重复着平面化的苦难故事,难以达到作家们所期望的文学高度。余华就说,他正是出于对这种小说的唾弃而开始写作的。
80年代的“寻根文学”则是全然不同的文学潮流。韩少功和阿城等作家感到中国文化中逐渐生出一种虚无主义,并对此深感忧虑,“寻根文学”就生于这股忧虑。他们认为,在五四运动和文革期间,不论是为了顺应还是抵抗西方文化,都逐渐忽视了中国丰富的地域文化。鲁迅曾经建议中国作家只读外文书,通过“硬翻译”的过程引入外文语法,但现在作家们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自我隔离来杜绝西方文学的影响。莫言和贾平凹等作家转而挖掘古老的农村传统、地方传说与知识,甚至是老旧的菜谱,摸索着那些在中国极速工业化进程中被忽略的故事。他们为自己的作品难以翻译而自豪。虽然西方经典无法被完全忽视,但可以被摆弄改造。在文革时期,阿城在靠近老挝边境的国营农场工作时,常常给同伴讲述《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将其中人物和习俗改编成中国风格,以促进听众的理解。
在2014年,习近平重申了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明确的文艺工作观。“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他宣布:“(文艺工作者应该)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然而,与1942年相比,文学不再那么事关重大。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曾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文学如今已成为一个与其他行业无异的小众产业。这不一定是坏事。数十年来,西方出版商把中国文学看作一口鲤鱼池,从中挑选中国的哈维尔和昆德拉(异见作家)。然而,当作家们不再背负着为人民发声的内部压力和成为异见者典范的外部期待时,中文虚构作品和诗歌有了更广阔丰沃的创作空间。尽管在习近平治理下审查力度有所加大,中文创作还是有着一定喘息的空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外界完全连接,不再背负着展示乡土特色或重复苦难故事的职责。
3
近年来,美国和英国的外交专家似乎纷纷发表反对中国的作品,如《长远之计: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他们提出的论点非常简单:中国想要消除民主体系并推行集权主义。然而这种投射式的论述相对于批评中国,更多地说明了西方国家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事实是,在当今主要大国中,中国是第一个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放弃其历史性宏图的国家。早在70年代,毛泽东就决定暂缓那些以他名义向非洲、亚洲及其他地区传播农民革命的共产主义团体。在1971年,毛的得力助手周恩来甚至提供资金协助平息斯里兰卡的一场毛泽东思想起义。换言之,中国早就停止了输出乌托邦的计划。这使得今天的美国成为最后一个仍然相信其制度应该被全人类效仿的大国,尽管这一信念已不如从前坚定。
在90年代,百姓依然可能认为,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的精英阶层在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稳定世界秩序。所谓的“反恐战争”就是这种现象的巅峰,每个大国都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精准而严厉的打击:美国与欧洲在中东和非洲、俄罗斯在车臣,中国则在新疆。随着全球化的承诺伤害了各国百姓,民众对全球精英间的利益交换产生了反抗,新旧力量的冲突逐渐浮现。在重庆,一位颇具魅力的官员薄熙来看到了一个机会,将民众的不满打包成一场新民粹主义、复古毛泽东主义的政治表演,挑战了当时北京政府与西方的全球化共识。薄熙来虽然失败了,但习近平似乎从中汲取了教训。习近平上台以来,共产党愈发不容忍繁荣带来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同时加强了意识形态上的管控。借鉴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打击商界精英、尝试清除腐败官员、强化新闻管制,甚至关停了英语辅导产业这类不平等的源头。
2022年,当美国政府庆祝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气候投资(计划在十年期间投入3690亿美元)时,中国在同一年投入了5460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领导者的地位已毋庸置疑,尽管其在资源开采区的行为有待质疑。同时,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力图保持回旋空间。中国支持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同时又担忧着美国和北约把这场战争看作包围中国的演练。关于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中国政府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间谍软件交易的同时表示武装斗争是对压迫者的“合理”回应。在许多方面,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使其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意识形态“问题”。尽管常常脱轨或与政策相悖,国内的社会主义理想依然是切实存在着的。
在上海你可以清晰感受到习近平政权下中国的社会矛盾。这个城市正在恢复其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地位。我拜访了住在法租界豪宅里一位所谓的中国“红色资本家”,这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媒体大亨常在西方社交平台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辩护。豪宅的外墙上涂着文革标语,花园中有孔雀在踱步。这位红色大亨以一种轻松愉悦的优越感接待了我。“如果民粹主义者再次接管白宫,你们美国的寡头怎么办?” 他问道。“中国留学生到美国之后变得更亲华了,这对你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继续调侃道。“奥巴马写《无畏的希望》的那几年,习近平在起稿森林管理相关的论文!你说谁更划算?”
第二天,我去附近的另一座豪宅拜访了当地的作家协会。长走廊的尾端,青年文学杂志《萌芽》的编辑人员正兴高采烈地忙着做新一期的刊物。而另一条走廊的尽头,早被掏空的《收获》杂志备受尊敬的编辑们摊躺在椅子里吞云吐雾,疲惫地望向空洞的远方。后来,我和上海作家云生去外滩散步,我们走访了一系列的上海书店。她在一家巨大而空旷的书店里跟我说:“这家是中国版Instagram的宠儿。” 那里的书都排放在难以触及的架子上。我们走进了满是红白封面的房间。“这是党刊专区,再往那边看就是亨利·基辛格专区。” “如果我们把中文版的《格兰塔》包装成党刊,这里有机会进货吗?” “别这样指望。” 她答道。
在《皮村》一文中,记者张含带我们参观了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庄,那里一群外来务工的作家通过书写自己的生活来寻找意义。萧海(音译)就是其中一员,他写着自己在90年代南方沿海“繁荣”时期辗转工厂生活的经历。他的文字精准有力地呈现着炙热生活的切片,供读者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宣称要创作“服务于工农大众”的艺术,而讽刺的是,如今当党的要求实现了,它却对这样的结果不屑一顾。

北京郊区的皮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