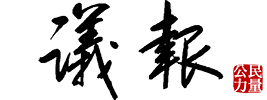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十六年后,2018年中囯政府提出争取三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愿景。然而,五年过后,国际社会仍然没有看到这一愿望“修成正果”。与此对应,“仲裁案”(菲律宾Vs.中国 2013-2016) 八年之后,南海局势并未好转,中菲在南海的对峙已常态,冲突朝向失控方向发展。中国作为南中国海最重要的当事大国,除习惯采用的政治-外交方式外,是否需要从法律层面对南海危机的解决有深入考察?
1.“仲裁案”中两个关键实体性事项的难题
“仲裁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共同关切。
中方对“仲裁案”中关于“九段线”和“历史性权利”两个实体性事项的裁决予以全面批驳:“仲裁庭错误处理《公约》与历史性权利的关系并错误否定中国在南海拥有的历史性权利。”(中国国际法学会,2017:188)仲裁庭认定“历史性权利不能超出《公约》规定,或者已为《公约》所取代的观点是错误的。”仲裁庭“脱离中菲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错误处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同前,2017:185)中方一直强调在《公约》生效很久之前中国就已经在南海存在并行使的“历史性权利”。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菲在南海争议》白皮书的引言中,中国政府申明“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国务院新闻办,2016年7月13日) “…… 早在1948年,中国政府就在公开发行的官方地图上标绘了南海断续线,确认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杨洁篪,2016年7月14日)
“历史性权利”是中国对南海(“九段线”范围内)权利声索的来源和基础。“九段线”的法律地位(是主权性质?还是其他性质?)则是南海争议的核心。因此,在解析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利之前,有必要对“九段线”的来历、初衷和法律地位做一简要分析。
1.1“九段线”: 初衷和法律地位
南中国海 “九段线”(台湾方面通常使用“U形线”的表述,)最初出现于 1914年,那时只包括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韩振华,1988:355)。后经二十世纪30年代三次变化(1933,1935和1936年),至1947 年 12 月 1 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确认“U形线”,对南海诸岛屿重新命名,并并将其划入海南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辖范围。(邹克渊,刘昕畅,2017:97)但是,从1947年正式公布至2009年之前,中方(包括海峡两岸政府)对于“九段线”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台湾政府在1993年南海政策纲要中称之为“历史性水域”- 但其中仍有许多争议和矛盾之处)。中国学者对此评论说“尽管该线问世之初未被明示含义和性质,但从 1948 年断续线产生到 2009 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并未表示疑义或异议。”(贾宇,2015:194)应该承认,持续60多年中各方的这种不清楚、“未表示疑义或异议”与中方的作为或不作为直接相关。“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南海 U 型线中历史性权利不甚了解甚至有重大误解,这与中国政府历来未明确‘U 形线’的法律地位有关。”(邹克渊,刘昕畅,2017:92)

贾宇在对“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的系统研究中注意到“九段线(断续线)的这种法律地位不明的状态:
“‘1958年领海声明’未就南海断续线作出规定。1992年的《领海及毗连区法》的规定中包括了领土组成条款与南海诸岛。该法将南海断续线内的四组群岛包括在内,但(仍)未就断续线本身作出任何规定。”(贾宇,2015:195,196)及至在1998年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依然没有言及南海断续线,……”(同前,2015:196)
南海的这种模糊-混沌的法律地位一直持续到2009 年,“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外交照会,抗议越南以及越南、马来西亚共同提交的外大陆架申请,并在文件中附上了有 “U形线”的南海地图。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联合国提交采用形线维护其南海主张的外交文件。”(邹克渊,刘昕畅,2017:99)顿时,“这条线及线内海域的法律性质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贾宇,2015:194)当然,笔者认为这种“初衷不明”模糊状态并非意味着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的作为是无的放矢。追溯历史背景,在1945年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大陆架声明后,中国政府面临接收二次大战后在南海的日占岛屿等使命。是故,初衷可能(笔者至今未检索到任何这方面有说服力的文献,故只能主观猜测)是要控制南海岛屿与其中的资源。但先后因疲于战争(1946-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朝鲜战争(1950-53年)以及此后大陆从50年代至70年代20多年一系列政治运动等原因,国共(两党)政府此后均无暇、无力、更无心关注此事,从此搁置,没有后文。这也可能是当时采用11段虚线画图,而不用实线的原因。须知,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国与国的疆界都以实线标明(虚线往往表明有争议或是未定国界/疆域-如:朝韩“三八线”、巴以之间边界线等)。
总之,中国创设该线的初衷至今没有被正式澄清,“九段线”的法律地位长期不明,这为围绕“九段线”产生的南中国海争端留下了长期隐患。
面对来自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疑问,应国际与国内政治之需,2013年菲律宾提起仲裁后,中国学界相应大力加强了对“九段线”和与其相关的“历史性权利”的研究,南海争端中的这一焦点得以开始从长期的“战略模糊”变为逐渐清晰。
“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一文对“九段线”的法理属性曾做出认定:“考察南海断续线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之后,依然难以从正面得出确切的关于南海断续线法律性质的结论。(故此)笔者尝试反列名单,采用排除法以图趋近答案。”(贾宇,2015:198)该学者依次排除了以下四种对“九段线”的(法律)界定:1)国界或海疆、2) 岛屿归属;3)历史性水域 4)领海基线、领海外部界限和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界限(第四种观点更多人认为是历史性权利(线)。此外,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士存院长还提出了“‘U 形线’ 是基于‘主权 + 海洋法公约 + 历史性权利’的观点。”“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在‘U 形线’内享有主权,以及 《公约》项下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此外,中国在 ‘U 形线’内还享有历史性权利,例如,渔业权、航行权、资源开发优先权。”)(邹克渊,刘昕畅,2017:98)
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仍未对“九段线”的法律性质做出正式、明确的宣示,只是在颁布的涉海法规、发布的行政文件中反复强调“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强化主权立场的同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逐步重视对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利”的研究。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南海九段线是一条历史性的权利线,兼具历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权利的双重性质。”(高之国,贾兵兵,2014:内容简介)
“九段线”在历经60余年演变后,已经成为历来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主权的宣示,并包括对在这些岛屿及其周围海域中从事渔业、航行以及包括资源勘探开发等其他活动的历史性权利。九段线还可能具有作为未来海洋划界界限的剩余功能。……结论:“九段线”的法律性质与地位是主权和管辖权。(同前,2014:20)
上述学者对“九段线”的法律地位和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这一核心议题上的观点兼具权威解释和学理解释的双重意义。鉴于中国政府仍未正式宣告“九段线”的法律地位,若将这些学者对“九段线”地位和性质的论证与中国政府对南海的立场声明结合在一起,大致就可以推断出中国政府对“九段线”的基本法律定位:“九段线”兼有“主权+历史性权利+管辖权”的性质。如此以来,中国首要的是要对其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进行更严格、令人信服的举证。未来中国还要面对与南海主权声索相关的一系列更艰巨的权益主张的举证责任。
1.2亟待进一步厘清的“历史性权利”
1998年中国在国家立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第一次出现了“历史性权利”的概念。该法第 14 条规定: “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对此,有学者认为“该法关于历史性权利的规定,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不因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洋区域制度的建立而影响、放弃中国在周边海域享有和可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贾宇,2015:196)这位学者进而把“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具体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 对水域的历史性所有权,包括琼州海峡、四组(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水域;(二) 在南海的传统捕鱼权;(三) 在南海的历史性航行权 ;( 四) 对南海大陆架资源的历史性权利。(同前,2015:201-203)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历史性权利”,包括贾宇在内的国内外的法律学者仍在争辩、论证之中。
这里需要明确,国际法上迄今为止并未形成对“历史性权利”的明确定义或概念,这理当是学界与国际司法领域的共识。Andrea Gioia在“历史性所有权”(historic titles)一文中认为“国际法学界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宽泛的历史性权利的概念,包括领土主权、通行权和捕鱼权。”(贾宇,2015:190)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一概念仍在发展、演化中,它“并无明确的外延和内涵。”(邹克渊,刘昕畅,2017:99)。
更需要考察国际司法实践。历史性权利 ”(historic rights )的产生、演化与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 ”(historic waters)“历史性所有权”(historic titles)等一组概念密切相关。中方学者认为“《公约》在相关条款中使用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传统捕鱼权以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等“历史性”概念,确认了历史性权利规则的存在。”(加重号系笔者所做)(贾宇,2015:182)但稍后该作者也承认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尽管对这些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最后通过的《公约》未能就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所有权的定义、性质、要件等作出明确和具体规定。”(同前,2015:182)《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在484段回应仲裁庭的裁决中辩称“历史性权利在一般国际法上早已确立。”(中国国际法学会,2017:203)“批判”进而引用以色列法学家、外交家Yehuda Z. Blum的研究说“‘历史性权利’,通常指‘一个国家在国际法的一般规则下一般不能获得但通过历史性巩固的过程取得的一些在陆地或者海域上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又承认“历史性权利在国际法上并无统一定义。”(同前,2017:204)仲裁庭也承认,“‘历史性权利’一词在性质上是一般性的,用来描述一国可拥有的某种权利,该种权利在不具备特定历史因素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法的一般规则通常不能产生。”(同前,2017:204)“批判”一书(485段)得出结论说“历史性权利由一般国际法调整”(意即不归《公约》调整-笔者注)。
目前中国学界主流与政府趋于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国对于南海的各项权益主张,很大一部分源于习惯国际法,例如,历史性权利的主张等 。”(邹克渊,刘昕畅,2017:97)依据这种观点,即便《公约》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依据习惯国际法仍然可以主张“历史性权利”,进而据此权利应辩对方(或任何争端中的另一方)在《公约》下所赋予的权利。在对“历史性权利”的认知上,“批判”注意到该权利的不确切、不稳定性:“基于国家和国际司法实践,历史性权利可以是主权性的,也可以是未达到主权程度的历史性权利。仲裁庭也承认此点。就达到主权程度的历史性权利而言,主权也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就未达到主权程度的历史性权利而言,可进一步分为排他性的历史性权利和非排他性的历史性权利。”(同前,2017:204)之后,中方对这种莫衷一是的复杂状况进行了归纳总结:“历史性权利基于国家实践和历史事实产生,历史性权利的种类和性质具有多样性,历史性权利所涉水域也具有多样性。为判定一国历史性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必须基于相关国家的实践、相关地区地理和历史的具体情况,个案处理。”(同前,2017:209)
如此以来,在一般国际法上对“历史性权利”定义不明、内涵和外延不清的前提和基础上,中国将一般性的“历史性权利”引入、适用于本案的具体案情来支持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就成了应辩中的一大技术难题。应该看到,中方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但从仲裁或诉讼的角度看,这些研究远不够充分、严谨。试以上文提到的贾宇发表在中国法学研究最顶级刊物上的研究为例。她归纳认定的中国在南海的“四大历史性权利”中第一项是“对水域的历史性所有权”(包括琼州海峡、四组(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水域(贾宇,2015:201-203),即是指中国对这一“群岛水域”拥有所有权-主权。然而依据现行《公约》相关规定,除对四组群岛中的极少数符合规定的岛礁可以合法拥有12海里(领海海域)的主权-所有权外,任何一国都不能合法的对借由零零散散的极小岛礁连接、构成的这片巨大水域(约200多万平方公里)提出笼统的“所有权”的声索。况且,中国作为大陆国家主张“群岛水域”(或曰“远海群岛”)的权利在本案之内和之外都大有争议;至于第二项在南海的传统捕鱼权和第三项历史性航行权则并非为中国独家-排他享有,其他沿南海国家(菲律宾、越南等国)更加临近南海,从历史到如今天然的能够更加便利的航行和捕鱼,所有这些南海国家当然都平等的(甚至可以更优先的)分享和使用这些权利。至于在对第四项“对南海大陆架资源的历史性权利”的认定上,作者忽视了“大陆架”作为国际法上的概念始于1945年的基本事实。无论从科技发现、勘探-开发能力还是法律依据,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主张“对南海大陆架资源的历史性权利”,换句话说,对南海大陆架资源(主要是油气和矿物资源)的权利只能是在当代具有的科学和技术能力、从现行的条约法-《公约》中产生,无法从历史的习惯国际法产生!
综上所述,与菲方依据《公约》赋予的明确权利相比,中方依据习惯法提出的“历史性权利”相对模糊,论证不够严谨,应辩缺乏说服力。可以预见,除非中国在自己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上给出符合国际法(国际习惯和/或国际条约)的清晰的界定和充分有力的证据,中国的“九段线”及其“历史性权利”主张将会不断被削弱、或者中国主动修改甚至淘汰。与此同时,中国将面对来自各方越来越大的挑战,导致冲突的解决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2. “仲裁案”之后:中国亟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
在对争端追根溯源的同时,中国需要进一步在“仲裁案”之外对与争议密切相关的三个基本问题做深入、严格论证:
第一,国际习惯法的识别和认定
中国学者强调认为“中国对于南海的各项权益主张,很大一部分源于习惯国际法,”(邹克渊,刘昕畅,2017:97)其中首先包括历史性权利的主张 。中共党媒批评道“仲裁庭…对习惯国际法熟视无睹。”(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因此,对国际习惯法的识别和认定对中国在争端中的权利声索就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列举了国际法渊源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包括“(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于1947年成立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履行国际条约法编篡等职责的同时,也特别关注国际习惯法的发展,为此从2012年起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论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最终成果收录在联合国第六十八届会议的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中(联合国,2016:A/71/10)。 其中第五章正式以“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为标题,通过了由七部分组成的“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草案案文”。与中国在南海“历史性权利”主张直接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在以下(国际法委员会)做出的5个结论中(联合国,2016:A/71/10:73-74):
结论 2 两个构成要素 要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及内容,必须查明是否存在一项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一般惯例。
结论 3 评估两个构成要素的证据
- 为查明是否存在一项一般惯例及该惯例是否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而对证据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到总体背景、规则的性质以及有关证据所处的具体情况。
- 两个构成要素中的每一要素必须单独予以确定。这就要求评估每一要素的证据。 ……
结论 8 惯例必须具备一般性
有关惯例必须具备一般性,即必须足够普及和有代表性,还必须是一贯的。
- 只要惯例具备一般性,就不要求特定存续时间。
论 9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要求
- 关于一般惯例须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要求作
为习惯国际法的构成要素,意味着有关惯例的采用必须带有一种法律权利或义务感。
-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一般惯例不同于单纯的常例或习惯。
结论 10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证据形式[1]
-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证据可有多种形式。
-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证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国家名义发表的公开声明;官方出版物;政府的法律意见;外交信函;国内法院的判决;条约规定;与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府间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有关的行为。
- 在有关国家有能力做出反应并且有关情况也要求做出某种反应的情况下,对一种惯例经过一定时间而没有做出反应,可用作已接受其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证据。
(联合国,2016:A/71/10:73-75)
上述“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中的各个结论对中国在争端中强调依据习惯法产生相关权利的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鉴于围绕这一焦点中方与裁判庭之间有重大分歧,因而这份报告中的结论及其详细评注对判定孰是孰非意义非凡。中国应当以此为原则依据重新审视以往针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以国际习惯法(包括历史性权利/主权/所有权等)在内的所有权益主张。对照这份清单认真回溯、核查,由此便可以基本确认自己提出的主张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程度如何。在此过程中,同时要注意区分一些基本(却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关键概念:国际习惯与国际惯例等
和法律关系的区别和联系。(李伟芳,2005:55 )他们的法律定位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此外,在国际习惯法的识别过程中,法律确念的意义对认定中国的主张十分重要,这是中国特别应加强论证的薄弱环节。
第二,如何平衡处理援引国际习惯法与适用国际条约法(主要是《公约》)之间的“冲突”关系
中国强调以国际习惯法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同时却忽视了(抑或时忘记了?)自身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所承担的《公约》当事国在条约之下的义务,因此是否应检讨有片面强调某一方面之嫌?中国部分主流学者至今没有厘清其强调的“历史性权利”-一种仍未达致成熟、稳定,尚未被国际公认的国际习惯(抑或是国际惯例?)与其已经承诺的《公约》下义务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其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第123条(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第74条(专属经济区)和第83条(大陆架)200海里划界规定之间的张力。除此之外,中国还要面对如何以惯例法的理论来论证、支持中国以后更多、更大的海洋权益(如,主权权利),赢得国际社会(而不是主要只对国内权威和民众)承认的挑战。中国明智的选择或许是在强调从习惯国际法(可能)产生权利的同时,重视《公约》明确赋予的现实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就南中国海的实际情形而言,尽管《公约》的规定仍有各种不足,但与习惯法相比,作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国际条约,其作用与价值仍然不容低估。当然,这并非指《公约》不可被质疑、甚至挑战,而是强调任何此类作为必须深思熟虑、严格论证,清楚预见到这样做的后果与影响。从以上对“仲裁案”相关部分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在处理援引国际习惯法与适用以《公约》为主的国际条约法关系方面明显失当,不利于争端朝向解决的方向发展。
第三,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
检视中国应对“仲裁案”表达的观点使观察者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处理该争端上所采用的是国内法与国际法二元论的立场和方法:国内法与国际法互不相干。即,通俗讲:“你说你的;我说/做我的”。倘若中国是持一元论的观点,那理当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或者国内法优于国际法。无论怎样二者都应保持一致。而中国的做法似乎在理论上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至少在国内立法上是要与相关国际法的规定一致),实践中却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给人一种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割裂的印象。对此需要引起注意:1949 年国际法委员会在《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第 14条宣称:“各国有责任遵照国际法及国际法高于各国主权之原则,处理其与他国之关系。”(R. P. Anand,1986,II:37) “约定必须遵守”是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从司法实践看,中国既然在批准、加入《公约》时已经严格审查了其与国内法相关规定的关系,理所当然的,在适用国内法的过程中就不能、也不应与自己承诺的条约义务相抵触,从理论到实践保持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一贯性而不是割裂或相反。
中国的特色政治体制决定了中方目前在处理国际、国内纠纷中仍然沿用以党的政策替代法律的“家常习惯做法”,以国内的思维方式来解释、适用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影响、甚至左右了对争端的分析和认识,导致与国际社会公认的看法不仅不合,甚至有时截然相反,给解决争端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总之,在南中国海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内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涵盖了《公约》规定的内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航道、空域等各种不同法律制度;涉及领土-岛礁归属、海域划界、各种资源(渔业等生物、油气、矿物等)开发、利用、航行与飞越、海洋科研、海洋环保、公务与民事使用、军事与和平利用等众多领域各种活动的调整和管理。在如此浩瀚又复杂的海域中,任何一个南中国海争端当事国如果忽视《公约》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都有可能招致不同程度的国家责任。对中国而言,还需清醒的意识到: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大陆国家,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争端过程中需要经历从观念到机制的根本改变,包括从人治到法治、由大陆意识向海洋意识;从“九龙治海”、各自为政到整合强化管控海上危机的系统改进。中国一直在强调“历史性权利”,但同样不可忘记的是在追溯、主张这一权利的同时,留心反思中国在国家发展、经略、管理海洋事务中的“历史性的教训”。借助“历史性的反思”,将有助于中国从历史上的“大陆人格”蜕变成现代的“海洋人格”,从而有清晰的意识和整合能力来管理包括争端在内的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海洋事务。
3. 小结:中国面对的考验与可能的择决
南中国海争端不仅兼有政治与法律的复合性质,在两者背后更有当事国经济文化以及国家政治体制特质等多重复杂因素。由于南中国海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目前突出表现为地缘政治与军事上的敏感与重要性,但争端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则是相关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决策、运行机制。一方面,国际社会不应轻视争端解决的艰巨与复杂性。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相信:争端或迟或早总要得到解决。对现阶段而言首要的是争端主要当事国的判断、决断与行动。毋庸置疑,在历史重大变迁之际,中国正面临着严峻考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一道,作为中共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九大报告”,2017:10)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汎关注。然而,以严肃、务实的态度看,中国若要真正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仍需要经过一系列处理国际国内事务危机事件的测试与考验。诸如:如何平息海峡两岸的阋墙之衅?能否妥善解决南中国海争端?这些只是涉及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两个典型实例。只有妥善处理好诸如此类的国际政治中的治理难题,中国才有可能逐渐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拥戴。而在上述危机治理过程中,南中国海争端(以及台海危机)与中国发展大战略的实施之间的必然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在一项(“一带一路”框架下)“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南海争端解决的影响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对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产生积极影响,而争端则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最大挑战’。(杨泽伟,2016:31,35-36)。试想,南中国海争端不解决,“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台海两岸案剑拔弩张的对峙不从根本上消除,何来和谐并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必须在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整体长远战略与近期局部策略之间的做出轻重、得失的艰难择决。何去何从?
事实上,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仍然可以有积极的作为。目前首要的是做对的事情-做出正确的择决。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为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已经投入了难以胜数的人力和财力,积累了许多很有价值、具有可操作性的成果。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争端当事国有义务在《公约》第九部分规定的基础上,以此为决策基本框架,进而做出新的解决争端的努力。该部分第123条规定了“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的国际义务,涉及生物资源、环境保护和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这是突破冲突困境、朝向南中国海合作开发的直接法律依据。与此相关的还有《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的规定以及与《公约》第九部分相对应还有“21世纪议程”第二部分第17章“保护大洋和各种海洋,包括封闭和半封闭海以及沿海区,并保护、合理利用和开发其生物资源…”。这是联合国为世界各国提供的明确的行动政策指南。
就目前南海冲突现状而言,在法律和政治层面推动建立新规范和制度的时机不成熟,可能近期很难有所突破。但对一些争议相对不敏感的领域,尤其是在当事各国间具有共同-相同利益的环境生态养护与资源开发领域可以有意识的尝试逐步推进新规范和制度的建立。这方面近年由CSIS组织完成的研究项目“Defusing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 A REGIONAL BLUEPRINT”(CSIS,2018)中在草拟的(各方)“行为守则”框架下,为南中国海争端亟需处理的两个优先事项,即渔业管理和环境合作;油气生产合作草拟了行动蓝图(CSIS,2018:6-17)。 中国多年来一直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外界也一直在“听其言、观其行”。中国相关决策部门应该对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予以应有的重视,秉持“诚信”(bona-fide)精神以获得互信,将“共同开发”的愿望与政策化为实际行动,以此向国际社会证实作为一个崛起的、有自信的泱泱大国是“言而有信,信而有果”。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是真诚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应该、而且需要做出明知的择决。
南中国海是一典型的半闭海。这一自然属性特征对该海域周边国家的国际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法律-政治和经济意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这种自然属性客观上要求南中国海区域周边国家合作开发、共同发展。事实与依据再明显不过,在《公约》和“21世纪议程”框架内推动建立环南中国海国家共同开发合作区不仅利在当代、更将惠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中国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中国能够与其他国家一道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一重大择决吗?国际社会正拭目以待。
[1] 其他结论详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