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储安平衣冠冢落成仪式在宜兴西郊外龙墅公墓举行,储安平的儿子储望英、储望华、储望德等至亲悉数出现在墓地前,伫立雨中,寄托哀思。作为子女代表,储望华在墓前讲话,之后,俯身亲吻了父亲陵墓前的无字书石雕。储安平在文革期间受尽折磨,最后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现在尸骨无还,落葬无骨灰,也没有逝者生前衣物,只是一帧塑封照片、一本塑封书籍,包裹在一方红布里,装入公墓管理方提供的一只陶坛内。正如储安平子女邀请的亲友代表、著名学者章诒和在她的讲话中所言:“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2015年5月19日储安平衣冠冢落成仪式现场
应该不是巧合,历史上,五月十九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九五七年的那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在毛泽东不断号召不断加温下,当天,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鸣放大字报。紧接着,各种大字报纷纷出炉,整个学校立时处在大鸣大放热潮之中,也带动了全国各行各业进入“帮党整风”的热潮。北大“五一九”运动喊出了“民主”和“法制”的口号,但不幸的是,也让毛泽东施展他的“阳谋”进行“反右”找到了口实。
储安平是其中著名的一个打击对象。他因“党天下”言论,惨遭毛泽东“引蛇出洞”迫害,至今位列五大不准翻案的右派之一。拙文撰写于十六年前,不过是对惨遭迫害的右派分子制出的一支卑微的安魂曲,是祈求历史正义的一次弱小的呼喊。当年超过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惨遭迫害,今天仍活人世的可能不过三四千人,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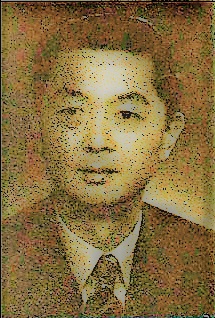
储安平遗照(1909年11月5日-1966年?)
但此文写作的那个时代,社会上人们多少还是心怀期盼的,本人也期盼中国能够深化改革开放。记得完稿当天晚上,悉尼作家刚好有一个聚会,欢迎天津作家杨显惠来访。他的纪实小说集《告别夹边沟》,描述右派分子劳改中大批死亡的骇人听闻的惨烈故事,当时让千万读者深受震撼,在中国评价很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此书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这个观点也是当时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此后不久,我刚好去中国,无独有偶,五月八日离开悉尼,当晚到达香港,第二天无意中就在香港凤凰卫视看到一套纪念储安平的节目,让我相当感动。四海同心,心同此理,我又一次感到人间正气长在。此文写作十年之后,储安平终于在老家“下葬”。当时有人希望“储安平衣冠冢让如烟往事沉淀”,我就说,对“反右”中种种冤案,对极其冤屈的文字狱言论狱,当然不会就此轻易“沉淀”,但储安平衣冠冢的落成得到了宜兴市政府的默许,怎么说还是值得称赞的。然而,许多善良的人万万没有料想到,就最近短短几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竟然急剧全面恶化,不要说什么希望中共当局对至今已超过一个甲子的“反右”运动做到正确评价、全部平反;相反,完全可能的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观点将会再一次遭受清算批判,而且更加严厉更加恐怖。君不闻,“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今天已经成了金科玉律;全面“姓党”、“定于一尊”,已经不容许一丝一毫的质疑。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正在把“天下”打造成一党的也就是今上一人的“天下”。
真是恍若隔世!正是在如此恶劣的局面下,人们更加赞叹和珍惜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真知灼见。
一

居住在悉尼的储望英与夫人陶俊英(本文作者摄于2005年6月30日)
那天在马白教授家里和储望英聚会。望英君是储安平长子,移民澳洲也有一些年月了,就住在悉尼南区离马白教授家不远的地方,过着平淡幽静的退休生活。我们谈那场倏忽之间就摧残了几十万精英的所谓“反右运动”,谈他父亲。他话不多,看来性格也像他每天的生活一样,但内心的悲怆,虽然压抑着,也是可以感觉到的。
二
关于储安平,至今还是一个谜——是他之死,或不知生死。
许多人已为此写过文章,提供自己的见解。例如:徐铸成的〈我的同乡〉(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孙琴安和李师贞的《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董乐山的〈闲话〉(广东《随笔》,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胡志伟的〈中共文化百人志〉(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余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以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一书中有关章节……等等。各有各的说法:“投河自杀”(在北京某个地方?)、“蹈海而死”(在青岛?在天津?在塘沽?)、“虐杀毙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掀起“红色恐怖”期间,北京市被打死或受到迫害后自杀者超过一千七百人)。也有说未死的,说储安平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或说他在江苏某地出家当了和尚……
最神乎其神的是章诒和的叙述: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坐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章诒和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这位大右派章伯钧的夫人没有兴奋起来,只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储安平的后人也不相信储安平还活在世上。储望英的弟弟、现在墨尔本居住的储望华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他父亲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储安平想到死是很自然的。而储望英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的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情景:他父亲被野兽吃掉了。他以平静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储安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可能神志不清地躅踯到北京郊外像八大处一带的山林里,那时八大处山林里常有豺狼野狗出没……
储安平孤零悲惨的最后日子又是怎样的呢?人们知道,反右之后,储安平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弃他而去,此后经年,大多数时候,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天只能与屋里养着的山羊为伍……
经过多方回忆,总算拼凑出一些零零碎碎的情景——
储安平“失踪”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
八月三十一日,刚好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惨受多日凌辱毒打的储安平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但没有成功。一个多星期后,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储安平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他踽踽离开家,走了出去……而阴差阳错,就在第二天,他学农的女儿储望瑞曾从北郊进城,回了一趟家——只见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东西也荡然无存,只是满地撒着花手帕,她记得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

储安平生前和子女的一次合照
九月中旬的一天,储望华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问知道不知道储安平目前在哪里。储望华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负责此事,并要求储望华和他二哥协助。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储安平曾有来往的朋友,却毫无结果。
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储望华,说他们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储望华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储望华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储望华一时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储望华是否和父亲彻底地“划清了界线”。他们知道,储安平最疼爱他这个自小聪明伶俐、天资过人的小儿子。
在那个全国笼罩在红色恐怖的年代,这种考察几乎是多余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九六九年,大阴谋家、迫害狂康生发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害人的恶魔显然都想清清楚楚确知所害的结果——他们引以为荣的业绩。
没有答案,即使在威严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死人无言,生人不语。真是一个冷冰冰的“死结”!储安平生死之谜,云遮雾障,扑朔迷离,如今虽然过了几十年,听来也令人分外黯然神伤。
三
作为一九八零年“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别”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究竟犯了什麽滔天大罪?历史庄严地记录下来了:“党天下”。

“反右”期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
储安平是在毛泽东“诚恳”动员之下,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发言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第二天见报于《光明日报》,标题改为〈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储安平说:
……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储安平的发言石破天惊,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而个别政治敏感者或有特别渠道者立时觉察到,这位“言者无罪”者肯定罪责难逃,要大大倒霉了。事实上,毛泽东于半个月前,也就是五月十五日,已写了一份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秘密文件,在高级干部中内部传阅。毛已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

当年一次批判储安平大会的入场卷
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诉,白天黑夜的、马拉松式的轮番轰炸,是从六月六日下午开始的。当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向世界公开地拉开了反右的序幕。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六月十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首先在吴晗的主持下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六月十三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也批判了储安平等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
六月十四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一致“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当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二十四个人发言,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
六月十五日,《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题为〈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
当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文章《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六月二十一日晚,九三学社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六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加编者按登载了储望英被迫于三天前写给父亲的公开信。
七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文章〈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文章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文章〈编辑“能手”〉。文章最后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八月六日,《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文章〈“党天下”—— “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
九月二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文章《天下究竟应属于谁?〉,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
十一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文章〈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天,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参加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余人,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
上述的远远不是完整的纪录。这些东西今天读来真是令人厌恶之极,因此不必再多录述了。不过,应该还加上毛泽东七月九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当然,“伟大领袖”不屑对储安平一人发话,他训斥全部右派,说:“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储安平〈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在1957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
在全国性的恐怖政治高压下,谁都要对储安平进行攻击、谩骂。为了尊重历史,我也不避讳列出储安平亲朋好友、不久前的战友同志,对他的攻击,其中包括后来同样被打落水者。“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戴晴在她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中如是说。一下子横遭众叛亲离的打击,储安平彻底崩溃了。他在“人民”面前成了大“罪人”,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储安平能有他想吗?“人民”一词,在党政治文化术语中,藏掖着深刻的诡谲。
早在六月二十一日晚,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储安平发言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
七月七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在七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七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右派们的自我批判收集成书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不结束。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93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于1957年11月12日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以毛式的形象又刻毒的时髦语言概括之,储安平已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下篇:https://yibaochina.com/?p=244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