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瞻
自2020年1月中国政府隐瞒、传播、扩散新冠病毒至今,已经转眼两年。此时此刻,全世界处于新一轮的病毒肆虐中,而中国疫情再起,当局则变本加厉、重演比武汉两年前更加丧心病狂、胡作非为、倒行逆施的反人道举动。为铭刻历史、记录罪恶,特地发表之前书信两封。白居易《登西楼忆行简》诗中有“风波不见三年面,书信难传万里肠”句,今改“风波”为“生死”后用作本文标题,更足见我们不幸所处国家和岁月的惨烈与苍茫。
简札一、在这苦难的时刻,我不流一滴眼泪
——致当年我北大的学生、现美国著名商学院终身教授H
2020年2月
H:你好!
昨天我们通电话,期间你几次叹息武汉人太惨了、武汉人真惨呀,说每次看武汉消息都要流一阵眼泪。之前,我的北大师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和博士导师L在一个我俩共同的群里写道:“每天都在扎心中度过。”

2020年2月,武汉随处可见的染疫病人倒毙在无人理睬的医院诊室里的情景。
听着、看着你们的语言和文字,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理解、体会你们的沉痛和悲伤,但却偏偏难以唤起感同身受——所以只能沉默。
“灾难、不幸一类的特殊时刻,能最真实最清楚地考验和显露人性”,这句老掉牙的话此刻同样准确。面对着人间地狱和惨无人道,我不由不直视和拷问自己:在我一向自认为脆弱、敏感、温柔和悲天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是暗藏着残忍无情的海下冰山?
我相信我变了,不知不觉的随着时间变了;我从没有刻意,但却一天天变得心如铁石。我女儿五个月时候,不论见到谁都永远是一副憨厚灿烂的笑容。后来一本育儿书告诉我,这个月龄被称为天使阶段:这是人类几万年进化成的本能,因为此时脆弱如悬丝一般的婴儿必须讨得成人的钟爱和呵护才会有安全、顺利的生命存续。与此类比,在这个乱世里、在这个躯体和灵魂被煎灼剐割的炼狱中,一个人不无声无息的演变到或表或里的残忍,就根本无法生存。卢梭说“政府的性格就是人民的性格”,我是政府治下的臣民,就像被狼喂大的人类,除了豺性一无所有。我时而大头症起来,会恍惚以为本人是先知、哲人,但病状一退立即清楚自己只不过是个诸事不能免俗的凡夫。所以,我既不会像美国人一样动不动就为旁人的苦难流泪、像香港人一样动不动就为别人的灾患捐资,也不会因自己的冷漠而自责——即使有人指控,我也会像彼拉多指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我女儿五个月时候,不论见到谁都永远是一副憨厚灿烂的笑容。
李敖翻译英国玄学诗人约翰.邓恩的布道诗:“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能自全,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虽然人前我如上般振振有词,但在中庭落花、别梦依依的静夜,我依然有一种顾炎武“亡天下”式刻骨的凄凉和悲哀:始终以“一片冰心在玉壶”自诩的我,到头来还是被毒化和腐蚀。也正是基于邓恩,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一样,我无法全心全意地同情那些受难者,正像我受难时绝不要别人同情自己一样。“雪崩来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罪孽是每个人造成和纵容的,谁也不能逃脱责任——除了那些作恶者,也包括讴歌者,包括沉默者,包括旁观者,包括受难者,也包括文章作者自己。在中国千年的吃人史中,所有人都在吃人、被吃,每个人在被吃的同时也在吃着他人。从狂人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迄今已经整整过去了一百年,这期间,那个邪恶的Gespenst又再次吞下了多少模糊血肉、吐出了多少森森白骨!最新的2445个惨死的鲜活生命和永远无法确知数目的冤魂,不过是它盛宴间隙的一个茶歇罢了。2016年雷洋事件时,在一个北大群里我写了如下的话:“因为‘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因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为‘别人的丧钟,也为你敲响’,因为‘如果你一再沉默,当你成为刀俎下的鱼肉时,已经没有人能为你发声了’”后,在无数人喝彩的同时,也有小杂碎们的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让我顿生牧首般的快感和垂怜以及革命家的愤怒和决绝。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大修罗场的武汉,不是依然有着数不清的人在恨之入骨、咬牙切齿的诅咒和陷害着方方,在热泪盈眶、感恩戴德的讴歌着政府吗?官媒一向是无耻下流的,但这些,倒的确不是它在造谣。
多少年来,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我者谓我情商不够——因为我反复自伤自虐。但像“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帅一样,虽然在恋爱上我一地鸡毛,在大是大非前我却早已不惑:我坚信“冤有头、债有主”,我绝不因为别人的罪行去惩罚自己。八十年代邓小平评价伤痕文学时说:“哭哭啼啼,没出息”,排除他“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负面人性之外,此话也有可取部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流泪无助于弥补和告慰死者,反倒让宰割者一如既往的洋洋自得、轻蔑世人、俯视苍生、睥睨天下,反而导致亿万个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最终重新辉耀那些无耻自诩的“救世主”的荣光。
一月十五日,我写了一篇关于伊朗击落乌克兰客机的文章,先知先觉地标题为:“生错了地方就是一种罪行”。那时,武汉尚是华东形胜、盛世芳华、海清河晏、千骑高牙、“参差十万人家”,人人“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如颠似狂、企盼新春,却不知毒魔已临、死之将至,瞬间一切就要化为尘埃。那时,我正在北京和一个朋友朝夕相处。这个朋友出身中国最顶级的望族名门,不折不扣的皇亲国戚,家资殷富。她长居北美,其时正暂回北京。一次比较中美,她说:生活在北京没有感觉和国外质量有别,甚至更加舒适、方便和体面;别墅区有会所、游泳馆、健身房,咫尺之遥是国际学校、欧式商业小镇、进口食品超市;学校有全封闭纯净空气操场、家长都是外交官和国际大企业主管;“就说看病、住院吧,都说在国内难,但这对我们不存在”,她未卜先知似的说。对她的话我没做反驳,因为那个时候我同样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而人不临患难,会始终活在幻觉中,没有切肤之痛。如今仅仅一个月,她和亿万中国人一样应该梦醒:覆巢之下、玉石俱焚,船沉之际、片瓦无存;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在这九百六十万公里土地上没有人能够幸免和逃脱,不会因为你的出身、你的家世、你的居所、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的人脉有任何异同。我对一个北京人说,我们该感激的只是病魔放过了北京,如果它一旦光顾,我们和武汉人毫无二致:留下遗书“噩梦降临,大年初一,老爷子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就治,均告无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还是一床难求。失望之及,回家自救,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奄奄气息之中”后全家灭门的导演常凯,陪伴老父亲在医院排队八个小时、实在无力蹲在地上看着摇摇欲坠的父亲“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如此卑微和下贱”的年轻女子,绝望无助哭喊着一路追赶而后挣扎匍匐爬向载着母亲尸体疾驰而去救护车的小女孩,因为抵抗隔离被从汽车上拖下扭断脖子死去的无名女性,父母遭隔离后遗弃在家里无人问津被活活饿毕的唐氏儿……每每看到上面这些场面、情景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我丝毫没有对自己置身其外的庆幸,而是相信他们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我们同样都是毫无尊严、命悬一线、风雨飘摇的蝼蚁草芥,又有什么资格与底气去同情和怜悯武汉人呢?
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博文作家N前年和我有过一次争论,彼时我相信历史进步有其水到渠成的规律,现在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干吗那么急呢?”我说,他回答道:“我当然急了,至少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还生活在这么一个国家中和制度下!”痛定思痛、抚今追昔,检讨自己当时的误区,我想我的好整以暇,是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永远不需要再回中国、更不需要在她人之初就不得不日复一日听那些谰言和谎言呢?不论如何,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懂得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会像海.伍德一样,被王立军“驾鹤西去,化作青烟”。这种猛醒、这种觉悟,应该胜于哭泣和流泪对死难者的悼念吧?
此信写毕,拿给一个朋友看,他沉吟良久,回复我说:“这篇文字,象暗夜里的一束幽光,似乎也找到了未来的方向,但却嘎然而止”。他说的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没有记忆、没有反省、伸手不见五指的没日没夜世界中,一次次轮回、一回回反复、一遍遍醒悟、一再再迷途,还让我怎能不嘎然而止?
保重!
简札二、在时代的狂风和巨澜中
——致一位小读者YY
2020年8月
YY:你好!
昨晚看了你最后发来的两句话:“我真不喜欢今年这种局面”、“要是能快进就好了”——简单平实的遣词,如同静水深流,似乎隐忍着不尽的无奈与难耐,又好像在“说尽心中无限事”,也让我深深感染和触动。
我们怎么会共同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是什么人、什么力量把我们推到了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境地?我看过许许多多描写二战期间离合悲欢的文学作品,有部《战争风云》和《战争回忆录》我读了几十年,常读常新。书里写二战时,欧洲战火连天,人们逃离无门;但也只是在那块大陆上,其他地方之间、甚至从美国到欧洲,只要你无惧,就能如坐着打上蜡的滑梯一样前往;哪里像今天这样封关锁国、交通决断、哀鸿遍地、关山阻绝?在收到你的短语后,我浏览了一下网上从美国到国内的机票信息,至少到十月前,所有航班全是“暂无报价”、“暂无报价”、“暂无报价”,连叁万、肆万的天价也不复存在——航空史上,恐怕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诡异。

全球航空业近于停顿。

疫情中的纽约曼哈顿。

所有航班全是“暂无报价”、“暂无报价”、“暂无报价”。
我现在过着纯粹遁世隐居的生活,周围碧草深树、秀水明湖。我是一个能够独处和静的下来的人,我可以不需要外人外物外界的平衡与支撑、不需要喧嚣和群居而圆满地活着,为此我深感自豪和骄傲。我曾将近一个月足不出户、人不与语,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我常常奇怪为什么在监狱里对违反狱规的犯人最大的惩罚是关他们禁闭,据说一个星期之后就都快疯了——。李敖同样如此:在山居的时候,他不但不出门,连饭都让人从一个狗洞给送进来。当然,静修、禅练、反省、问心,等等这些我一概没有:但我会在一个小天地里忙忙碌碌而特别宁静、充实、快乐和悠游——更别说身边还有一个纠缠无度、让我日无宁日的小女儿了。只有在某个时候、某种触动下,就像昨夜月上中天、移步后园之际,我才会生出那种难以抑制的孤独、寂寞和惶惑不安,那种“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的迷离、悸动和痛楚。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对我就像瞬间一刹。每到临眠,我都草草看一下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字。今天全球新增17万病例、死亡近4千人;也就是说在我们山中一日、平平庸庸的同时,地球上有数以千计的生命在逝去。“环球同此凉热”,从来没有此刻般让人感同身受。上面说的网上中美之间航班一片“暂无报价”的字样,令我看了顿生核爆炸或者飓风横扫之后举目荒芜、寸草不生的印象。中国民族有一种浸入骨髓、挥之不去的丧亡离乱的心理积淀,王羲之的《丧乱帖》和杜甫的三别诗吟咏的都是这种集体记忆。近几十年里,人们误以为换了人间,今天才知道了流离距离我们既不久、也不远,而且随时可以重来。当然我不去深想这些,免得压抑绝望——自己闭门不出是一回事,但困居囚禁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2018年8月,毕业于北大的我的小师弟、安信证券首席分析师高善文在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有一个引起巨大反响、后来自己又缩头否认的演讲,其中得罪小糊涂虫们最多的一段话是:“我这个年纪无所谓了,可以静观其变;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这次(国家)没搞对,你们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这段话后来被简化成了:如果这次和美国搞坏了关系,90后的小朋友们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高善文讲话的时候,中美刚刚开始贸易战,还远远没有搞到今天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地步;如果当初只是一种假设,今天则注定成为无可逃脱的宿命。沉船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生——何况香港已死,我们不再有比悉、拉末、戈兰,这先知摩西为以色列人建造的三个庇护逃城了。所幸的是,我早就黄粱梦醒,如今连睡眠都不需要了。香港陶杰说到他这个年纪,已经明白什么改变民族性、改革国家,都不过是痴心梦想,今后不会再做此念,余生里要让自己丢掉家国情怀,去做一个国际人。不过他又马上慨叹道:可惜在疫情弥漫、满目疮痍的今天,连个当国际人的机会都不可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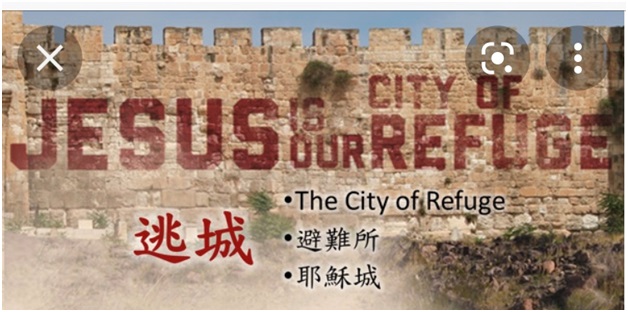
先知摩西为以色列人建造的庇护逃城。
按照越来越有共识的观点,第一波疫情还未有穷期,第二波或许当秋发生:所以眼前还远远看不到人类究竟哪一天才能恢复原状。唯一可以预见的是,疫情过后,世界将永远回不到过去,我们的生活也永远回不到过去。分离和阻隔将成为很多人的日常内容,我们会看到、体验和经历更多上一代人常态的、我们这一代人罕见的、你们那一代以前从未想象过的那种岁月。
此时,小女正在沉睡长鼾,面容像月光一般皎洁——真的是“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呀!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为了发微你的体会,为了共鸣你的感受,为了触摸你的心灵,为了抚慰你的焦虑,也为了铭志这乱世中的辛酸和悲欢,记下在时代的狂风里和巨澜中个人弱小命运的无常、寡助与挣扎。
谢谢你长期的鼓励、凝注、关切与爱惜。你所有的留言、来信,对我都是动人的温馨和巨大的慰藉。我虽无语,焉不动容?
最后我想对你说:即便我前面提到高善文的话,但我仍然相信,优秀的你会有着灿烂、美好的前程。我虽然鄙视后浪,正像我同样睥睨我的前浪和同浪一样,我也依然希望他们能生活在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再像他们的前人一样恐惧、扭曲、猥琐、下作和无耻。
多自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