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起)翟永明與唐丹鴻。(唐丹鸿提供)
在唐丹鴻寫翟永明的故事裡,有一句看似突兀的「她的眼睛確實像兩道傷口」,這種脫口而出源自對於唐丹鴻來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翟永明成名作《母親》:「母親,我的眼睛像兩個傷口痛苦地望著你。」而在翟永明的敘事中,糾纏唐丹鴻和注定被唐丹鴻糾纏的父親這個角色,就像她的「嗜睡」一樣,與翟永明的「失眠」和「母親」對仗並且同構,合成為「讓人深感不安的緊張和失衡」這一幣的兩面。 她們的寫作,因為不符合公主必須與女巫互掐然後需要由一個王子來吻醒的定制人設,而通常被視為一種叛逆或出軌——按照《聖經》的記載,她們的出現是在男性誕生之後,並且是作為男性的附屬品而存在的。然而,在伊甸園裡面對一隻熟透的蘋果時,她們卻先於男性開始了獨立思考,並進而在原罪的問責上,被代表男性至尊的父神唯一一次地顛倒了男女之間的主從關係,使她們從一開始就不僅要為自己、更要為男性的墮落負責。 因此,女性寫作與生俱來的身份焦慮,就如同母親的子宮與父權壓迫的宿命關聯一樣難以擺脫。也因此,她們的寫作一直是從男性視角中掙扎出來的過程,而這種掙扎所引起的叛逆和出軌的焦慮,令每一個從男性堆砌的文字中突圍出來的女性作家身上都有一道流血的傷口。這傷口便是她們的身份認同,而流血便是她們活著的生命象徵。 言小義
翟永明 | 痛苦不是可耻的
2000 年10月.我和唐丹鴻一直通过 E-mail 联系,她在信中不断重复的是“我走了⋯⋯”、“我回来了⋯⋯”、“我又要走了……”、“去藏区……”。藏区我是和她一起去过,蓝天阔地,雪山高云,我们俩都曾经为一个痛苦的理由到那里去医治过间歇性忧郁症,对我来说,并不比她的心理医生差,因此现在我身在德国柏林的一条繁华大街的背后,一座中产阶级司空见惯的公寓里,怀着嫉妒的心理读着她的 E-mail,想像着她在高原开心地笑,疯狂地恋爱和作爱,健康地拍摄和写作,忙碌得像个小蜂后。而我,却陷入她前两年的沮丧,无法写作,从早到晚看还珠楼主的 《蜀山剑侠传》(五大本,从成都带到柏林),它们是我在德国的心理医生。

时间退回 1999年,初冬,唐丹鸿打来电话,说要去楚布寺拍片:两个月,吃住都在那里。楚布寺两年前我与她一起去过,很美的寺庙.很野的环境,很苦的住宿,很酷的喇嘛。两天,太好了;两个月独坐青灯古佛旁,太难了。何况西藏的风很大,大到足以毁容,足以撕心裂肺,无处藏身。“你的脸⋯…” 精心呵护多年,准备交待给这两个月吗?
年底.我又接到电话:我回来了。带回来的还有“楚布寺”和“吉吉尼玛”。接风洗尘,我惊讶她的瓷器一样的脸依然微澜未起,光洁如桃子表面。她谈起睡通铺,不洗澡,吃糌粑,屙野尿,我不敢相信是那个当年化妆要费时近一两个小时的女孩,那个大白天蜷伏在书桌上睡了又睡,喝完咖啡接着睡(又一个让我羙慕的理由) 的女孩。就凭这两个月,我真的服了她,她说要感谢她的心理医生张血曦,让她从一种病态中恢复了新的生命力。那时我才知道她已开始做心理分析。
这两三年,我们就这样在来来去去和慌慌张张的状态中坚持一种联系,接头暗号是“回来了”,接头地点是白夜酒吧或万象纪录片公司,接头目的有时是一顿火锅,有时是一首新写的诗,有时是一次私密谈话.最后是《夜莺》……
2001年2月,在我准备重整旗鼓的白夜酒吧,首映了唐丹鸿的《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这也是我俩筹备的“白夜影会”的首次放片。我选择它不仅仅是因为姐妹情谊,更因为它是成都唯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作人制作的纪录片(到現在仍是)。片长180分钟,片比1:7,人物三个,摄像两人,演播场所乃一不足60平方米的酒吧,一切都不在常规中,却吸引了成都的好多艺术界、媒体界人士和闻讯而来之人,把“白夜”挤得满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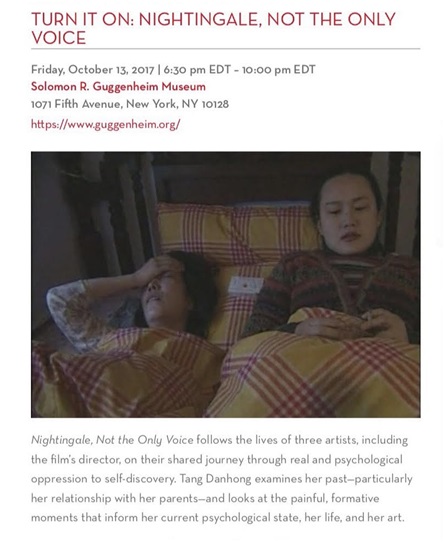
片子开头是成都街景,司空见惯,后来出现了行为艺大家尹小峰.画家崔萤。崔萤对着镜头哭个不停,唐丹鸿固执地质问父母,不厌其烦地与心理医生谈话,话题弥漫,意乱心迷。表面上看,也有一些调侃的因素,尹小峰胡言乱语,唐丹鸿脱衣洗澡,包括崔萤长达十多分钟的自述,但潜伏在其下的是让人深感不安的紧张和失衡。三个人其实都在一种无序的景况中表观或者说表演一种无方向的,但又类似自画像般的真实。生活的狀态不是行云流水的,
片子的节奏也不是,这里面有导演的固执和极其私密的心理挣扎,拍摄和剪辑的关注点都显得怪异,日常而又非常,想说的和想表达的在 BATACAM 镜头前都变形了,四分五裂了。多数东西她都曾对我讲过,也在诗中暴露过,没想到会变成图像扑面而来,比平面的感受更让人震动。她既比我勇敢,也比我坦率,敢于面对困扰她的一切问题,不像我对其中的残酷遮遮掩掩,永难了断。这也是我羡慕她的另一个理由。
影片中她质问父母的一段让人吃惊,她就像“挤疮里的脓水一样”要挤出父母和自己身上的黑暗和无情,并咬紧牙关要让世人看到这一手术过程,爱、痛苦、思索、观看,都成了一种向外扩大的暴力,摄影机,她自己,父母,观众和靠她最近的人都能感觉到这种后坐力。

(影片《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劇照。)
她所追问和质疑的与父母的关系肯定是迄今为止最直截了当的。我不敢说我完全能接受和信任这种方式,我的方式肯定更曲折。曾有一位德国人看了我的诗 《母亲》之后说他为诗中一种对母亲的“恨”所震惊,而我听了后比他更震惊,因为那是一种一直被我认为是“爱”的东西,就像在这部片子中感受到的一样。是我们已经无法区分血液中爱与恨的化学性质,还是它们根本上就是同一种成分?
清算父母肯定比清算自己更可怕,所以焦虑有时会占上风,片长和剪輯时不舍得割爱带来的冗长也加强了这些焦虑,好孩子与坏孩子的游戏至今还在纠缠,处于巨大的矛盾之中的她,终于把自己弄得像个“痛苦发生器”,强迫症式地把这些不稳定因素一股脑地塞给观众。她说:为了解脱的折磨。她拍片,她说:“拍片像一个代肺”。她通过镜头和剪辑机这两片肺叶,交替着洗滤痛苦,自由自在地呼吸,通过把朋友和自己的沮丧,不快乐,歇斯底里,对爱的渴望一一展示出来.告诉那些坐在电视机旁保持良好心情,睁大眼睛看她要干什么的人:痛苦不是可耻的,可耻的是不愿承认自已感受到了痛苦。至于片子的结尾,就像问题的答案,手术的疗效,都不是她最关心的。她匆匆地同时也是心烦意乱地缝合自己和朋友和父母和童年和后期和剪辑的伤口,就像她每一首诗的结束,戛然而止。
唐丹鸿 | 我生命中的一个象征
1986年夏天,当时我是一名大学生,我很想坏掉,一边与一个相对来说让父母称心的男孩交往,一边与一位看起来放浪形骸的校园诗人打得火热,因为他送给我一本地下诗歌刊物《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里面有翟永明、柏桦、莽汉主义等诗人的作品。我的父母可能到死都不会明白那些诗怎样摧毁了他们的期望并把我变成了让他们的更年期充满尖叫和失眠的女儿。我不知诗人们散布在哪个角落,我没见过他们中任何一个的面孔,这让我焦急得心脏隐痛,唯有亲近我的诗人男友,唯有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闷热的或凉爽的傍晚,我与男友照例约会,他因事要找翟永明,把我也带上了。

她住在科分院西物所(我母亲也在那个单位)的一幢充满煤烟的旧楼里。踏上一级级散落着烂纸和饭粒菜汤的楼梯,经过杂七乱八堆着簸箕、扫帚、只容得下一个半人穿过的过道,敲开一扇遮着布帘的木门,我见到了她。
那是一种梦中的母马与她身旁孤独摇晃的幼苗的相见。她在屋里来回走动,递烟让座,同三个男人交谈,她客气地招呼我喝茶,叫我“小唐”,她的眼睛确实像两道伤口,她的乳房大得像涨满了乳汁,她的骨节粗大的手脚与马蹄可以相互嬗变……我缩在屋角的板凳上,处于像看见眼皮内膜上游移的彩斑和金星的精神状态,只感到我之外的高大、温和与芳香。
我有一个嗡嗡响的在闷黑颠簸的子宫中的二十岁,我已经濒临憋死,否则上天怎会派出男友、地下诗刊和诗人降临世间,就像在肉厚腥臭的黑色天幕上撒出噼噼叭叭的焰火,焰火踮起脚尖跌落之处翻涌出怒放的花朵……从此我的生命有了一道裂缝,仿佛我是一个单细胞终于分裂了,在那之前我叫唐丹虹,在那之后我是唐丹鸿;从此,包裹我的那层腥臭密实的黑膜有了一道裂缝,一丝光使眼睛诞生,一丝氧气使肺存在。
那本《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中,有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中的《预感》和《七月》,有普拉斯的《爱丽尔》。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这册地下诗刊销魂蚀骨——就像童年时在严冬紧紧搂住自己的热水袋,用脸贴着热水袋,亲吻这个热水袋,爱着这个热水袋。

透过厨房油污的玻璃,有时是躲在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后面,有时就在她身旁,我注视一个女人:她梳理她乌黑的披肩发,她进了阳台侧面的洗手间,她切菜,她伏在水盆上洗脸,她的腿像吊桥升起又落下那样骑上自行车从我的视线消失……我常常猜测她的腹中有没有小孩?为她所爱的人是谁?
她就是翟永明,在我们成为邻居的那两年,我就处于这种状态,我为此感到痛苦和难为情,又感到快乐。我常装得跟她很随便,很轻松,甚至放肆……十几年过去了,她把我看成一个朋友,她有时搂着我照相,或抱着我跳舞,我依然幸福得晕眩。当我们把一杯杯酒咽下喉咙,在我趴下之前,我渐渐地忍不住对她提到了这种感觉,她有些难为情地笑了起来,我又憋回去了……
现在我的年龄比她初见我时的年龄还大了,仍然依恋着她。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我知道有好几个女人早在我之前就对她开始了这种依恋。只要回顾与她交往的这些时光,我就会涌起感激和爱……有时我又觉得她很柔弱,就有强烈的想保护她的冲动,但我发现她事实上充满力量,那种柔弱只不过是涅磐的表面……我为她感到骄傲,她是最优秀的。总之,翟永明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象征。我们姑且称之为“联系”。

(翟永明《痛苦不是可恥的》原刊封面。)
生活经历也造成了我们的区别,这当中有秘密而复杂的故事,难以在此陈述,但有些线索是明显的:比如她失眠,每个夜晚都使她恐惧,她老醒着,竭力睡;而我,有太多的睡意,如她所说“婴儿般”,我嗜睡,竭力醒……现在她更宽容,而我更粗鲁;她更能忍耐,而我更暴躁;她基本上表里如一,而我有时装模做样;你可以从诗里,特别是我们最近写的诗里,从现实中都能看到这种“区别”。(本文是在唐丹鸿2000年书面答王艾、宋逖的相关访谈基础上进行的修改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