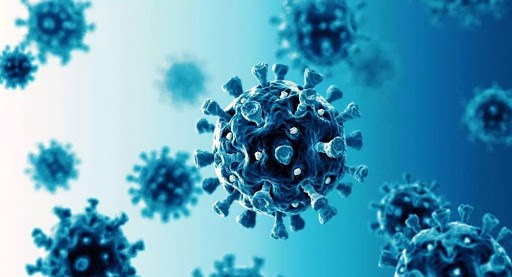在最近的一次放大电话中,安德森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俯瞰着太平洋。他告诉我,他最初的怀疑反映出他对冠状病毒的了解还不够多。他说,他使用 “疯子理论 “一词,部分是指当时流传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声称SARS-CoV-2是用H.I.V.的基因插入设计的。他还在早期的讨论中把自己称为疯子,他说,因为他对病毒工程的怀疑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我认为有些人认为我是个白痴,因为我甚至认为它来自实验室。随着大流行病的发展,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自然来源的解释。人畜共患病的蔓延可能需要蝙蝠和人类之间的中间动物,但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物种。最初,武汉的华南市场出售鱼类、农产品和肉类,似乎是SARS-CoV-2的来源。在最早的174个已知病例中,近三分之一与华南市场有关。然而,零号病人很可能不是。中国官员说,他是一名中年会计,姓陈,12月8日出现症状,通常在河对面的一家超市购物。2020年5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说:”起初,我们认为海鲜市场可能有病毒,但现在市场更像是一个受害者。新型冠状病毒早已经存在了”。
在怀疑论者中,其中许多是有信誉的科学家,其他是业余的网上侦探–包括一些完全的QAnon阴谋论者–另一种理论形成了。武汉是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所在地,自第一次SARS疫情以来,该研究所已经积累了世界上最大的蝙蝠冠状病毒库之一;约1.9万个样本储存在其实验室。它的科学家与国际病毒猎手团队密切合作,在领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从美国政府获得数十万美元的研究资助。W.I.V.还经常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该中心在2019年秋季将其实验室迁至华南市场附近的一个新地点。
支持一种新说法的间接证据–大流行病可能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事故开始的——在2020年底开始积累。W.I.V.的在线数据集消失了,关于以前爆发的信息被忽略了,而且W.I.V.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工程病毒的实验。甚至安德森也承认,病毒在武汉的出现是 “一个疯狂的巧合”。2021年5月,一群著名的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信,呼吁进行认真对待实验室泄漏假说的起源调查。随后,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2019年11月,三名W.I.V.研究人员出现了类似COVID-19的症状,并寻求医院治疗。
作为回应,拜登总统呼吁对该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调查。”我现在已经要求情报界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可能使我们更接近明确结论的信息,”他说。国家反扩散中心的任务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该中心被选中来促进这项工作。根据8月发布的调查结论的非保密摘要,该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开发的,它的突然出现让中国官员措手不及,并且它感染人类的时间不晚于2019年11月,”12月在中国武汉出现了第一个已知的COVID-19病例群。” 否则,所有机构都认为有两种来源假设仍然是 “合理的”:”自然暴露于受感染的动物和实验室相关事件”。
2012年春天,在云南省通关镇附近清理一个废弃铜矿的蝙蝠粪便的六名男子,患上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他们被送入昆明的一家大学医院,医院将其中四名男子的血样送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新发传染病中心主任石正丽的实验室。石正丽是中国最著名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者。几年前,她加入了一个国际团队,发现马蹄类蝙蝠是大量与SARS相关的病毒的储存库。她的实验室对工人的血清进行了检测,以确定石正丽和其他人之前发现的可能的人畜共患病原体。一切结果都是阴性。其中三名工人死亡。
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石正丽和她的团队定期前往距离武汉约一千英里的通关矿区。晚上,研究人员在矿井的一个入口处挂起了一个雾网,等待黄昏时分,蝙蝠飞出来觅食。从六种不同种类的马蹄蝠和紫斑蝠身上采集了咽喉和粪便拭子。最终,石正丽的团队为他们的实验室带回了一千三百多份样本。
2016年,石正丽和她的同事发表了一篇来自这项工作的论文,发现许多蝙蝠同时被两种或更多不同的冠状病毒所感染。由于蝙蝠挤在不断变化的群落中生活,它们无休止地循环着病毒,甚至跨物种,这使得不同的病毒可以重组,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菌株:这是一场进化的狂欢节。最终,石正丽的实验室将对从通关矿区采集的样本中发现的所有九种与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的某些部分进行排序。
三年后,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石正丽收到了来自七名患有新型病毒的病人的样本,这种病毒正在悄悄地肆虐武汉。一旦石正丽对这种病毒(SARS-CoV-2)进行了测序,她就在W.I.V.数据库中搜寻任何基因匹配的证据。根据她和她的同事在2020年2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她发现的最接近的亲属是一种蝙蝠冠状病毒,与SARS-CoV-2有96%的相似之处。她称其为RaTG13。”Ra “代表蝙蝠种类,即Rhinolophus affinis,或中间马蹄形蝙蝠;”TG “代表地方,即通关;而 “13 “是它被发现的年份,即2013年。
在几个月内,印度的一对科学家夫妇Monali Rahalkar和Rahul Bahulikar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联系——石女士在她的论文中没有注意到。在网上发布的一篇预印本杂志文章中,他们说,根据他们的遗传分析,RaTG13似乎与Shi在2016年关于废弃矿井的论文中描述的一个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样本 “100%相似”,但名称不同。RaBtCoV/4991。奇怪的是,石正丽的两篇论文都没有提到当初带领科学家前往废弃矿井的患病工人。
一个名为@TheSeeker268的推特用户向拉哈尔卡和巴胡利卡发送了一个链接,链接到一篇关于这六名工人疾病的2013年硕士论文。作者是昆明医科大学的一名医学生,他写道,这六名患者接受了抗病毒药物、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的治疗–类似于COVID-19的治疗。一位知名的肺科医生对其中两名患者进行了远程会诊,并诊断他们患有肺炎,主要是病毒引起的,可能还有继发性真菌感染。这位医科学生得出结论,这些肺炎病例很可能是由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引起的,这些病毒从矿区的马蹄蝙蝠身上溢出。2016年,由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指导的一名学生的博士论文(也是由@TheSeeker268发掘出来的)中的后续章节指出,其中四名患者的血液样本,经W.I.V.检测,有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抗体,表明之前有感染。
在这些发现被公布后,《自然》杂志发表了石正丽的RaTG13论文的附录,承认了与矿区的联系。石正丽澄清说,她的实验室在2018年对RaTG13进行了全面测序,因为 “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和能力已经提高”。她还提供了她的实验室对工人血清样本进行测试的细节,并表示实验室最近重新测试了这些样本,这次是针对SARS-CoV-2。他们都是阴性的。她还说,没有发现类似SARS冠状病毒的抗体。
这些工人没有感染SARS-CoV-2,否则我们会有COVID-12,而不是COVID-19。但是在一些科学家中,缺乏透明度引起了质疑。像W.I.V.这样的实验室被期望向世界警告可能构成威胁的病毒。在通关,有一个小型的威胁生命的疾病爆发,它看起来像SARS,但不是SARS,在一个矿井中密布SARS样的蝙蝠冠状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对受感染的工人只字不提,即使他们的病例与大流行病有直接关系,直到独立的研究人员确定了这种联系之后。
@TheSeeker268是DRASTIC(即调查COVID-19的分散式激进自主搜索小组)的成员,该小组在推特上成立,是实验室泄漏理论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Rahalkar和Bahulikar也与该组织有松散的联系。) 在一条关于W.I.V.研究人员和通关矿的推文中,@TheSeeker268写道:”简而言之。他们没有对他们的矿场之行、他们旅行背后的动机以及他们取样的所有CoVs进行说明。”
石正丽坚决否认她试图压制有关通关煤矿的任何事情。”我刚刚下载了昆明医院大学学生的硕士论文,并阅读了它,”石正丽告诉BBC。”这个结论既没有证据也没有逻辑。但它被阴谋论者用来怀疑我。” 相反,她在去年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时说,一种真菌是使矿工患病的病原体。”石正丽说:”蝙蝠粪便,覆盖着真菌,在洞穴里到处都是。真菌感染对探矿者来说当然是一种风险。但它们也是肺炎病例中常见的继发性感染,正如在一些COVID-19患者身上看到的那样。
新加坡杜克大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项目主任王林发(Linfa Wang)是世界领先的蝙蝠病毒专家之一,并经常与石正丽进行合作。他曾帮助分析2012年从工人身上采集的样本,并驳斥了对石正丽保密数据的指责。”我们想证明冠状病毒导致了死亡,”王林发告诉科学。”如果我们证明中国的人类中存在另一种类似SARS的病毒,那将是科学上的辉煌。”
2019年9月,根据DRASTIC存档的网页,一个曾经公开的W.I.V.数据库被禁止访问。它包含与大约2.2万个样本有关的记录,其中可能包括通关的序列。当被BBC问及此事时,石正丽说,W.I.V.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其网站和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 “受到了攻击”,因此数据库 “出于安全原因被关闭了”。这些数据仍然没有被提供。
在RaTG13和SARS-CoV-2的基因组之间有一千二百个不同的变异,显示了进化的混乱。这些突变的数量和分布太大,RaTG13不可能是SARS-CoV-2的直接祖先;它们至少在20年前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分裂出来。但是它的基因接近意味着 “我们应该在发现像RaTG13这样的亲属的地方寻找SARS-CoV-2的祖先,”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进化生物学家Jesse Bloom在9月告诉我。”在这一点上,已知SARS-CoV-2的最接近的亲属存在于两个地方:云南的蝙蝠洞和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撇开地理因素不谈,武汉病毒研究所及其合作伙伴进行的实验的性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5年,石正丽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冠状病毒专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是《自然》杂志一项开创性研究的共同作者。通过使用开创性的基因技术,巴里克研究了哪些病毒结构可以使冠状病毒有能力感染人类。这项工作涉及合成所谓的嵌合病毒,该病毒以神话中的野兽命名,其部分来自不同的动物;在这种情况下,SARS的一个改良克隆与石正丽在云南发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的尖峰蛋白相结合。
他们的研究发生在病毒学家的一个充满争议的时期。四年前,一位名叫Ron Fouchier的荷兰科学家决定看看他是否能使致命的禽流感病毒H5N1更具传播性。在未能从基因上重新设计病毒后,Fouchier转而采用一种经典方法:他将病毒反复传给活的雪貂,迫使病毒在新的宿主身上进化。十轮之后,该病毒在空气中传播。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创造了一种可用于大流行的病原体。
该实验构成了一种被称为 “功能增益 “的研究类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有高层会议、专栏文章和报告谴责这种工作的风险远远大于它的价值。2014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授权暂停涉及流感、SARS和MERS的功能增益研究,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监管程序。然而,巴里克当时正在进行他的嵌合病毒实验。他向N.I.H.生物安全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批准他和其他研究人员免于暂停试验。
当巴里克在人类气道细胞的培养液中测试嵌合病毒时,其穗状蛋白被证明能够与细胞受体ACE2结合,这表明该病毒现在已经准备好跳跃物种。在活体小鼠中,它引起了疾病。鉴于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巴里克总结说:”科学审查小组可能会认为在流通毒株的基础上建立嵌合病毒的类似研究风险太大,无法进行。
这并没有发生。巴里克的实验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继续进行,N.I.H.已经确定这些实验不是功能增益的实验。石正丽的实验室开发了自己的平台来创造嵌合病毒。她将来自云南的另一种蝙蝠冠状病毒–WIV1–与不同的新型尖峰蛋白的克隆杂交,并在人化的小鼠身上测试了这种创造。这些病毒迅速复制。其中一种病毒使小鼠变得憔悴,这是严重致病的迹象。使这项工作特别有风险的是,WIV1已经被认为对人类有潜在的危险。巴里克本人在2016年题为 “类似SARS的WIV1-CoV有望在人类中出现 “的研究中明确了这一点。
根据石正丽发表的论文,以及拦截组织获得的N.I.H.资助的拨款申请和进度报告,W.I.V.的这些实验中有一些是由美国政府资助。2014年,N.I.H.向一家名为 “生态健康联盟 “的纽约非营利组织提供了为期五年、价值370万美元的资助,其中一部分–大约60万美元–给了W.I.V.。(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取消了暂停,在经过三年的研讨会和多个机构的审议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监管过程)。) “不要误导人们,说我们多年来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福奇告诉我,他的声音提高了。”根据我们的定义,这不是功能增益,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定义,我们就改变这个定义吧。”
最近几个月,怀疑自然起源的人指出,石正丽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嵌合病毒实验,与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相比,后者不需要同样的预防措施,如完整的P.P.E.,对研究人员的医疗监控,强制性生物安全柜,控制气流,以及两套自动关闭的锁门。因为他们正在研究新型蝙蝠病毒,而不是已知的直接感染人类的病毒,所以低生物安全环境符合中国法律。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冠状病毒专家Susan Weiss,最近与安德森和其他人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概述了自然起源的证据,当我告诉她他们一直在BSL-2实验室工作时,她感到很惊讶。”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她说。
尽管如此,石正丽在嵌合病毒方面的记录工作都没有导致SARS-CoV-2的诞生。(“如果你想说那个特定的实验可能导致了SARS-CoV-2,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福奇说。) W.I.V.设计的嵌合病毒在冠状病毒家族树上离SARS-CoV-2很远。据石正丽说,W.I.V.在他们的一万九千个样本中只分离和培养了三种新型冠状病毒。然而,她的这一章工作所展示的是对风险的高度容忍。”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David Relman说:”他们基本上是在用世界上的专家认为准备出现在人类身上的病毒进行俄罗斯轮盘赌。”这是一种不顾一切地操纵它们的意愿。”
1月,世界卫生组织向武汉派出了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对SARS-CoV-2的起源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搜索。该小组的报告于3月发表,将人畜共患病的蔓延–从蝙蝠,通过中间动物,到人类–列为最可能的起源途径。他们认为实验室事件是 “极其不可能的”,在主要报告的一百多页中只有三页是关于这一理论的。正如安德森在调查证据时经常说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但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合理的”。
首先,自然起源有历史先例。2002年11月,在一个城市市场,SARS从蝙蝠蔓延到果子狸身上。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出现的MERS,从蝙蝠到骆驼再到人。果子狸在SARS爆发的四个月内被确认为最可能的来源;骆驼在MERS爆发的九个月内被确认。然而,SARS-CoV-2的中间动物——是目前唯一可以明确证明它不是源自武汉实验室的东西-——还没有被发现。这种发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正如W.H.O.任务的成员在8月写给《自然》的信中所说:”对中国境内外的人和动物进行关键性追踪的生物学可行性窗口正在迅速关闭”。
W.H.O.团队的一名成员是达扎克(Peter Daszak),他是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该联盟致力于缓解传染病的出现。自第一次SARS爆发以来,他一直是W.I.V.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为N.I.H.的分包合同提供便利,并与石正丽和她的团队在实地进行广泛合作。他坚定不移地为石正丽担保,并带头将任何关于实验室事故的建议称为阴谋论。”他告诉我:”这个实验室释放假说的问题在于,它取决于一件关键的事情:病毒在流出之前就在实验室里。但我知道那个病毒并不在实验室里。”
达扎克是一位广泛发表的疾病生态学家,他也知道自然界中病毒的多样性几乎是无限的。最近,他和其他生态健康科学家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冠状病毒可能从蝙蝠蔓延到整个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的人身上的频率。他们将所有23种已知携带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蝙蝠物种的栖息地与人类人口地图重叠。根据蝙蝠与人类的接触和抗体数据,他们估计每年大约有四十万人可能会感染与SARS有关的冠状病毒。”达扎克告诉我:”人们每年都会接触到它们。”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甚至可能生病和死亡。”
换句话说,溢出效应的发生远比人们意识到的要频繁。当人们在山洞里躲避,收获蝙蝠粪便–世界上最好的肥料–以及猎杀、屠宰和食用蝙蝠时,就会接触到蝙蝠,这在整个地区的不同地区都是有据可查的做法。”生态健康联盟的蝙蝠生物学家、最近研究的共同作者肯德拉-菲尔普斯告诉我:”这些小村庄处于正在消失的森林边缘。”在那片森林里有密密麻麻的野生动物,它们因棕榈油和水稻单株的侵占而受到极大的压力。” 受压的动物(就像我们一样)更有可能生病和感染病毒。
在这场大流行之前,习近平主席将野生动物养殖场作为一种扶贫手段加以推广,该行业基本上不受监管,雇用了1400多万人。”达扎克去年告诉我:”有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网络,人们参与耕种和饲养动物,并尝试新的想法。”这是创业,是混乱的,是那种半死不活的农场,里面有混合的物种。” W.H.O.的报告指出,武汉的一些野生肉类供应商位于中国南部,那里是寄生SARS类冠状病毒的马蹄蝙蝠的主要居住地。也许这就是病毒从蝙蝠传给动物的地方,而这些患病的动物被带到武汉,在华南和该市其他三个已知的活体动物市场上出售。”安德森说:”很明显,错过的最大机会是对这些市场的潜在宿主–中间宿主进行检测,不仅仅是华南市场,还有整个武汉,以及这些动物来自的更远的农场,据我所知,官方没有这样做。”
中国政府于2020年1月1日关闭了华南市场,并对其进行了消毒,基本上摧毁了一个犯罪现场。中国官员告诉W.H.O.的调查人员,那里没有出售活的哺乳动物–他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但他写道,湖北中医药大学的一位病毒学家一直在 “偶然地 “进行每月调查,以确定一种严重的蜱虫病的来源。6月,他发表了一份包含文件证据的研究报告,表明在SARS-CoV-2出现之前的两年里,代表三十八个野生物种的近五万只活体动物--其中许多现在已知易受SARS-CoV-2影响–在武汉市场(包括华南)被出售和屠宰。
2020年2月,中国禁止了活体野生动物的交易和消费。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养殖场被关闭。云南的一位农民说,政府买下了他的竹鼠,并杀死了他的恶作剧。中国官员没有分享他们在大规模屠杀前对农场动物和工人的测试程度。W.H.O.代表团在报告中指出,这使得 “任何早期冠状病毒溢出的证据越来越难找到”。中国官员告诉W.H.O.,他们的科学家确实测试了31个省的8万多份牲畜、家禽和野生动物样本,这些样本是在疫情爆发前后收集的,但没有发现SARS-CoV-2的证据。
世界上被贩卖最多的动物–穿山甲,最初被认为可能是中级动物搜索的竞争者,不是因为它们在华南市场出售,而是因为在2020年初,从中国南部边境的走私者那里没收的一群穿山甲的组织样本对一种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冠状病毒,但这种病毒很奇怪。它的部分穗状蛋白,即受体结合域,可以比SARS-CoV-2的更紧密地与人类ACE2结合。早在2020年2月,安德森就已经对SARS-CoV-2的ACE2结合强度产生了怀疑。穿山甲-冠状病毒的发现有助于改变他的想法。如果穿山甲自然演化出一种与ACE2结合的冠状病毒,那么SARS-CoV-2也可能自然演化出这样的特征。(穿山甲冠状病毒的其余部分与SARS-CoV-2区别太大,不可能是其来源)。)
从那时起,SARS-CoV-2的近亲已经在中国、泰国、柬埔寨和日本被发现。但是支持自然来源的最重要的发现是在9月宣布的。科学家们在老挝–就在云南的边境以南–发现了一种马蹄蝠冠状病毒,在基因上比通关矿区的病毒更接近SARS-CoV-2。它可能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从与SARS-CoV-2的共同祖先分裂出来的。令人震惊的是,它们的尖峰是相同的,并以同样的效率与人类ACE2受体结合。安德森说,这一发现 “完全粉碎了许多关于云南特殊的主要实验室泄漏的论点”。”这些类型的病毒比我们最初意识到的要广泛得多”。
布鲁姆对老挝的发现的意义提出质疑。”他说:”我不认为这真的,再次告诉我们这些病毒到底是如何到达武汉的。但是中国的野生动物贸易可能既是SARS-CoV-2这样的病毒的孵化器,也是一个转运系统,事实证明,SARS-CoV-2不一定适应于人类,而是更普遍地适应于哺乳动物。咳嗽的老虎在布朗克斯动物园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然后在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八只拥挤的大猩猩。白尾鹿有SARS-CoV-2抗体。在荷兰,该病毒摧毁了水貂养殖场,使68%的养殖工人受到感染,并加速了该国毛皮贸易的永久结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毛皮生产国。水貂养殖场会不会是问题所在?浣熊犬是中国毛皮和异国肉类的另一个来源,也是易感者。”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病毒跳到各种动物身上,没有任何适应,没有任何进化,”安德森告诉我。”它是一个通才。它必须如此,否则它可能不会引起大流行。它是一种独特的野兽。”
9月21日,DRASTIC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新启示。2018年,生态健康联盟的达扎克与石正丽、巴里克和王林发合作,曾向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交了一份价值1420万美元的拨款提案。该提案–从一个匿名举报人处获得–详细描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识别、模拟和测试与SARS有关的新型蝙蝠冠状病毒的溢出风险,然后为马蹄蝙蝠本身开发疫苗,以防止病毒跳入其他动物或人体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计划在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中插入 “人类特有的 “furin裂解点。呋喃酶裂解位点是SARS-CoV-2的唯一最突出的特征。亚利桑那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Michael Worobey最近说,它是 “这种病毒的魔法酱”。”无论它是天然的还是转基因的,这就是这种病毒在人类中流通的原因。”
在SARS-CoV-2出现之前,研究表明furin裂解位点扩大了病毒能够成功感染的宿主物种的范围,并增加了其传染性(这一假设已被大流行病证实)。为了让冠状病毒进入一个细胞,它的尖头必须经历一个脆弱的蜕变过程,即被切割成两块。只有这样,病毒才能与宿主细胞的膜融合,并卸下其遗传物质,或RNA。具有呋喃酶裂解位点的病毒可以利用宿主的呋喃酶–一种人体容易产生的酶–来迅速切开它的尖头。Worobey说,这 “有点像让病毒处于发令状态,因此一旦它与细胞结合,它就能进入并非常有效。
DARPA提案指出,科学家们将在实验室创建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版本中引入呋喃酶裂解位点,这些病毒是从云南的蝙蝠身上发现的。他们计划每年对三到五种新型蝙蝠病毒进行全面测序并产生克隆。然后他们将在人类呼吸道细胞中测试改变后的病毒,并有可能在人源化小鼠中测试。安德森说:”这描述的工作是,’让我们出去发现新的病毒’,””并做一些像furin裂解位点的事情。所以,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与更广泛的对话有关”
SARS-CoV-2是已知的冠状病毒家族树中唯一拥有一个furin裂解位点的病毒。”我们现在知道,有与SARS-CoV-2相似的全长蝙蝠CoVs,它们与人类ACE2结合得很好,”Bloom说,指的是老挝的病毒,”但只是缺乏furin裂解位点。” W.I.V.每年都在收集许多病毒。如果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与SARS-CoV-2更相似的病毒,对人类ACE2具有相同的结合亲和力,然后在实验室中把furin裂解位点换成该病毒的克隆,情况会如何呢?这样的工作可能直接导致了SARS-CoV-2的产生。”M.I.T.的Broad研究所和哈佛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治疗博士后陈(Alina Chan)最近在推特上说:”一个新的furin裂解位点可能是一种天然病毒从动物蔓延到人类并引起大流行的额外因素。”它也可能是实验室病毒跳入研究人员体内并被带出实验室而不被注意的额外成分。”陈是即将出版的《病毒——寻找COVID-19的起源》一书的作者之一。自2020年春天以来,她一直是可能发生实验室事故的最顽强的研究者之一。”必须要问的是,”她在推特上说,”为什么知情者不认为在2020年1月,让世界知道有可能导致SARS2在武汉出现的研究是紧急和重要的。”
该提案被拒绝。DARPA的一位项目经理解释说,其 “主要优势是经验丰富的团队和选定的冠状病毒热点洞穴,这些洞穴显示了新型蝙蝠冠状病毒的高流行率。” 但是,他们写道,该小组 “没有提到或评估功能增益(GoF)研究的潜在风险”。也就是说,该小组没有为他们的实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可大流行的病毒的事件制定计划。DARPA内部的审查人员对该提案的 “不负责任 “性质以及对功能增益研究所带来的风险缺乏考虑感到 “非常震惊”,一位未被授权与记者交谈的官员告诉我。
2020年春天,当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开始宣传实验室泄漏理论,将其从任何合理的讨论中劫持出来时,有人告诉他,EcoHealth的N.I.H.拨款资助了W.I.V.,N.I.H.突然取消了该拨款。当时我和达扎克谈到了科学的政治化以及这个决定将如何影响他的组织的运作能力。他说,这停止了与W.I.V.在重要工作上的合作,这些工作直接关系到开发COVID-19的药物,追踪病毒的来源,以及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的发生。他说,这也意味着EcoHealth的科学家将不再有机会获得W.I.V.的数据。”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他在描述EcoHealth在中国的工作时说,”中国科学家会尝试做我的工作,但这不会是同样的工作,也不会是我们真正理解下一次的工作。”
尽管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furin裂解位点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但石正丽、巴里克和王林发从未公开提到他们提出过这些实验。达扎克尽管是W.H.O.调查的成员,但什么也没说。(“所有这种furin-cleavage-site的工作都应该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而不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生态健康组织的发言人说。) 安德森强调说,没有证据表明提案中描述的任何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但他补充说:“实际上,看到现在发布的内容,我感到相当震惊。我认为,参与这项特定资助的美国研究人员没有早些公布这些信息,是一种巨大的伤害”。(生态健康发言人告诉我,”DARPA提案没有得到资助”,”所述工作从未完成”。)
杜克大学医学院的王林发是第一个公开讨论DARPA提案的成员。他最近与布鲁姆、沃罗比和陈一起参加了由《科学》杂志主办的辩论会,并在网上进行了直播。布卢姆和陈都问为什么不早点分享该提案的存在。在中国出生和长大,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现在住在新加坡的王林发说,他不知道从一个失败的DARPA拨款中 “发布信息的适当程序”。当《科学》杂志的作家和辩论会的主持人乔恩-科恩就透明度问题向他提问时,王林发说毛细血管裂隙部位不是他提议的部分。”从第一天起,我就说,要在实验室里设计一种冠状病毒,从技术上讲,这是可能的。但是从现有的知识来设计SARS-CoV-2?那是不可能的。”
我曾经感到奇怪的是,以目前的技术,病毒学家无法查看SARS-CoV-2的基因组并确定它是否被设计过。当我向一位研究冠状病毒的法国病毒学家提到这一点时,他冷冷地说:”秘密在于,如果你足够仔细地观察,你可以看到一个微小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签名。” 实验室泄密的支持者将他们的大部分论点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中国官员、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石正丽在他们拥有的病毒和他们所做的工作上说谎,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掩盖。自然起源的支持者认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经分享了一切。”不是科学家们不想分享,”Relman说,他在SARS-CoV-2的起源问题上一直避免采取立场。”而是他们不会被允许。”
各方的赌注都很高。从一个角度来看,证明该病毒有自然来源对中国来说更糟糕。如果野生动物养殖场对这一流行病负责,这将牵涉到习近平主席的政策。如果是实验室泄漏,那么只有一个或几个科学家要为一场事故负责。无论哪种方式,中国政府很可能更倾向于一场漩涡般的理论风暴,他们可以在其中继续推动自己的理论:美国士兵在2019年10月的世界军事运动会期间将病毒带到武汉,或者美国政府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制造病毒。或者他们可以指责进口冷冻食品。阴谋论从这里开始分支,在他们自己的一种进化树中。
如果中国不提高透明度,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找到真相。北京 “继续阻碍全球调查,抵制分享信息,并指责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情报界在解密的摘要中说。”这些行动部分反映了中国政府自己对调查可能导致的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对国际社会利用这个问题施加政治压力的挫败感。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及其盟国将继续 “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充分分享信息”,并在世界人权组织的第二阶段调查中进行合作,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拒绝这样做。
目前,两种理论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正如一位朋友最近对我说的,“为什么我们似乎必须选择一个阵营?” 两个阵营都希望了解其起源,以防止出现下一个大流行病。但是,在他们之间,有一些重点的不同。
实验室泄密者往往对生物安全、透明度和人类的傲慢更感兴趣。他们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追随金钱的动力,颠覆中央集权,颠覆学术等级制度,并揭露压迫性政府的不公正现象。有些人是中国的鹰派。总的来说,他们没有做过病毒猎取的实地或实验室工作。
在自然起源方面,大多数人都做过W.I.V.追求的那种野外和实验室工作–而且经常被大自然无尽的多样性所折服。他们相信科学的先例,而不是那些尚未解决的不确定因素。这个阵营中的许多人都把他们的职业生涯献给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卫生,并且多年来一直对未来的大流行病发出警告。溢出效应最常发生的原因是土地使用的变化,或人类对以前荒芜之地的侵占,这几乎在整个地球上都在发生,但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地区,如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
不止一位病毒学家提醒我,大自然是最好的生物恐怖分子。它比人类更有创造力。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进化能够实现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以及我们所不能想象的一切。”如果你看一下鸭嘴兽,你可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某个人设计的东西,对吗?安德森说。”因为它太荒唐了。这有点像一场灾难。但它工作得相当好。” 它占据了自己的生态位。安德森说,SARS-CoV-2的一些显著特征使它成为 “冠状病毒中的鸭嘴兽”。
然而,人类已经改变了这一方程式。将病毒称为人畜共患病毒掩盖了我们在其进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野外、湿货市场还是在实验室。当人类在一切事物中都有自己的手时,什么是生态位?自然界惊人的多样性包括人性。不知何故,SARS-CoV-2在我们身上找到了它的生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