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怡畫像。
言小義
一、“正如火星总要向上飞动”
想正本清源讲,王怡原本是诗人。
余世存说鲍勃·迪伦,“他的音乐成就使一般人忽略了他的诗歌和思想成就”。我想可以同样提出,王怡的诸多身份使一般人忽略了他的诗人身份及其诗歌成就。
说他是诗人,不仅因为各类写作中他写诗最早,也因为他多种门类的写作流淌着诗的语言诗的气质,乃至他的思维都具有摇曳生姿或燃烧不已的特色。老实说他“美得惊动了党中央”,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若就狭义讲,他的“诗龄”已达二十四年。一切开始于“爱情、信仰和诗歌/都沦为了私生活”的时期。据他自己讲,“……在我20岁到28岁之间,我与世俗生活的距离,几乎是依靠诗歌去调整的。再近一些,再远一点。诗歌是我在卑微的私生活中赢取尊严的唯一方式。”然后从2001到2005年,诗笔确实停顿过几年。可是从2006年妻子怀孕三个月起,怎么就再次提起诗笔,然后一发而不可收。大致数算了一下,光2015年一年,他就写了一百几十首。“创作热情”之高,实在让人惊奇。
目前人们能看到的他的诗集,也就两个——《秋天的乌托邦(1994-2008)》、《大教堂:二十年诗选》(1994—2014)。此外还从微博、微信上,随时看到新的出品。我在今年6月1号“王怡诗歌朗诵会”之前,由于近水楼台的关系,先读到了他已经结集、尚未付印的2014、2015两年诗选《神秘的哀悼者》,和尚未结集、也未定名的《变老的时代》几首诗。不敢说有所研究,也得说对他1994年迄今诗歌写作的大貌有所了解。意识到以前咋没认真想过,王怡骨子里是个诗人。很快想到他现在作为牧师,生命与时间几乎不属于自己——“在礼拜一,就想念手擀面了/礼拜二和加尔文在一起/礼拜三查经,礼拜四剪头发/礼拜五上午有婚前辅导,晚上祷告/礼拜六一直在忙/到了礼拜天,世界就结束了”(《小史诗:礼拜天》)……这种情况下他竟然诗思如泉涌,写得既好又多,实在让人想不通。
今天当个“诗人”,好像不算什么。但是我内心觉着,不是什么人都能写诗,更不是只要写诗就是“诗人”。总得写出一些好诗出来。而且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作为一名诗人怎么都得具有鲜明突出的诗歌美学。得有“人无我有”的印记。按照这一相对严格的标准,也得认为王怡是一位成熟的写作者。比如1996年《献祭》:“我之所以还能写诗/是因为勇敢的文字/出于怯弱的想像”。2000年《三月四日:隐喻》:“从一个词转至另一个词/之间光线幽暗/我缺乏必要的勇敢”;“一个顺手写下的单词/泄露了人生的全部隐喻”。同年底《命名、个人写作及现代诗》一文,更是揭竿而起的阵势:“文章是天下之公器。诗歌只可能是隐私”,“一个‘诗人’必须首先是一个‘私人’”。然后生怕人听不懂:
“现代诗之所以首先是一种命名,在于它已经和古典诗歌相去甚远。……如果我们不能从集体公社式的写作之中把作为个体的自己选拔出来,我们今天的写作就是无力为继的。我们的每一句诗就像风尘女子,我们的每一个词语都人尽可夫。就不过是构成一个语言的公有制帝国的螺丝钉。”
毫无疑问,他有自己的美学。但是怎么讲?也能看到变化的轨迹。我看到2013年,他致意“一切变幻不居的事物中/唯有语言的确美好/所有关于人的真理都已死去/唯有语言的确美好”(《唯有语言的确美好》),同时又机敏补充:“诗。是跪下去的语言/美。是站起来祈祷”(《读书笔记:诗》)。到2014年,像《饥饿的艺术家》一样,“他发现词语和生活一样辽阔/也和生活一样卑污……现在,他怀疑每一个词语/它们比这些年来经过他身边的女人/更加折磨他的心”(《饥饿的诗人》)。到2015年,“谁说一块土地不会说话/一片山林不知道任何事/世上有穿堂风,和能言马/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比喻/它们为此而造,为此而存在”(《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比喻》),却又……怎么说呢?认为诗人不如婴孩。同年提出“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一个汉语,可以颠覆一个政权。/十四行呢,可以颠覆一千年。//在秘密的化装舞会上,让认出你的人/认出你来。认不出你的,更加认不出你。”(《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同年还提出“诗人不可能不想到政治”,以及“我的诗句是伟大的残篇/隐约着,一种他们没有想过的可能性。”如此高调了,却又卑微:“主人,现在我只剩下语言/用来伤害和被伤害/用来祝福、咒诅和争战/现在,无人能夺走我的尊严/除非他夺走我的语言。”(《主人,现在我只剩下语言》)到了2016年,更是美学宣言一样写——《在这个冬天,我们靠一些词语取暖》:
在这个冬天,我们靠一些词语取暖
花时间安息,也花时间死亡
将一瓶贵重的油,缓缓浇在心上
然后扇动双臂,摹仿飞翔
请注意,是扇动,不是煽动
因为在这个冬天,火苗已经熄了
你必须把上帝比作不义的法官
或令人心寒的父亲
才能带来我们亟需的刺激
因为在这个冬天,必须有一些词语
给我们持续的电击
我承认,这是残忍的
但这不是实验,而是抢救
并且是和春天约会的唯一方式
——无疑,正如火星总要向上飞动,他不可能不是一个诗人。
二、“我的诗比尘埃更低”
长达二十多年的写作,是个漫长而饱含辛酸的过程。
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前面所引,对“现代诗”的命名与认定:“我所谓诗歌的‘个人写作’,甚至可以说等于精神上的手淫,是非常private的,是个体命运的一部分。只有这种方式的诗歌才是本真的,自由的。……这就是我的诗歌写作对传统写作的割袍断义,画地为牢。”——应该说,这是布罗茨基所传递过来的火把:“语言,我想还有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些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文学在对国家的态度上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
但是以2005年信主为界,诗人生命分为前后两期。他的诗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按照《大教堂:二十年诗选》的目录排列,从2001到2005是“中场:沉默”期,此前是“死亡”此后是“重生”。与之相说明的是,2005年6月《作为救赎的诗歌史》一文认定:
“对我而言,诗歌的路是救赎的路。从哀歌开始,到赞美诗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自觉:“……我在哀歌之中,中断了我的诗歌史。我的诗比尘埃更低,但作为救赎的诗歌史,有没有机会从赞美诗重新开始?……”的确应该说,他的诗歌从哀号开始。
确乎没有盼望。看《时代的初夜》:“那时我们诵读北岛的诗句/像一把刀子。那时我们多么骄傲”,而“一个时代倾注了我们的精血”。《献诗》:“创造历史的,其实是我们的影子/蹲踞在月光下那只雪豹/在山崖。默默流泪/它布下的阴影掩去远方的公路/面对镜像。你开始迷恋自己”。《一切边缘之上》:“红罂粟铺满我的足下/一切边缘之上/我梦见自己惊慌的面孔”。《墙》:“我们面对面伫立/因为孤单/靠着墙各自垂泪”。《结局》:“天国的门永远虚掩着/我们的眼横亘在半空/‘于天上望见深渊’/一只青鸟迎面飞来/在最接近的刹那骤然消失”。《油菜地》:“有多少灵魂在夤夜呼告/不甘心像树木。默默死亡”。
确乎比尘埃更低。即使“我看见太阳菊花般升腾。绽放/并坠地/我看见血红的花瓣在远方摇晃/就一直在想/能使阳光生长的阳光是什么模样”(《刹那》),终于还是“向着虚空/只伸出一根中指”(《玫瑰的火焰》)。自认“一个没有福分的人/像花粉。在时代的边涯/像花粉一样散播……像偶然的花粉/偶然的蝴蝶/偶然的上帝,将我们遗弃”(《上帝的花粉》)。遇上相信基督的农民时,“有一种变化在我内心/我心脑清醒。目光如炬/对他的皈依不可理喻”(《遇上相信基督的农民》)。甚至有《挽歌》,想去亲吻那枚柠檬般的圆月,“从十三层楼顶跳下去/你们后天便会忘了我”。有《遗言》:“我的脸庞如此生动/睡在冰凉的墓床”。《沉睡者》:“玫瑰花开的声音让我痛恨/恨自己不是那长眠地下的人”——嗯,不想引了。
确乎太灰暗了。1994年12月26日,为“蓉儿21岁生日”作《纪念日》:“我们本来陌路。活在彼此的欲望之外/如野草生于大地。天空有飞鸟离去……譬如风。譬如无邪之肉体/你只是一个喷嚏。就失去了我……时光的流里。我们只是不断坠落/惊慌中抓住了彼此的手/何等偶然的开端。白白的欢喜……除了我们躺下的地方/没有哪里。可以称其为家”。1995年12月26日,献给恋人生日的《故乡》:“那面床是唯一的故乡/我们反复躺下。又反复起来/如果。如果坟莹也能/反复的躺下/又反复的起来//用你的唇/爱抚我荒凉的脊背吧”。1996年8月5日《流沙》:“流沙是我的居所/我的房地产//一个被流沙湮没的孩子/在黑白的梦中数着沙粒”——嗯,实在不想引了,更不想评论。
不。完整抄录一首:
哀歌
很久不相信神话了
今晚。一个神话在我们耳畔悄悄发芽
今晚。梦见一个清瘦如柴的梦
美丽如夭亡的少女
如春日被人摘去的花
你不必说
你已化蝶
神指给我看了
凝固的海浪。安睡的鱼
和我指端
腾起的每一缕烟
很久不相信神话了
今晚。今晚的爱情像神话一样奇妙
今晚的耳朵听不见哀歌
今晚的爱情像神话一样奇妙
今晚的耳朵听不见哀歌
22岁时写的这首诗,明明写“爱情像神话一样奇妙”。只因“今晚的耳朵听不见哀歌”,因而“今晚的爱情像神话一样奇妙”。更奇妙的是,分明没有哀歌标题却是“哀歌”,实在让人不知有什么办法了……当然仍有“远去的河”,有“经过想像的爱情”,有“在那遥远的地方”,及“对古老生活的奢望”。有“秋天的乌托邦”:“你举着一只避孕套,经过春天的田野”。甚至“一切边缘之上”,还有“内心生活”。举个例子说,“面向一个纪念日/我举起双手/我就有权保持沉默”(《庆典》)。再比如《背叛》:“你们清醒时。我要睡眠/留给白昼一具缄默的肉体/和不满的鼾声//你们爱恋时。我要独身/面对欲望不动声色的积蓄/在你们阳萎的时代囤积居奇……”。没有烟抽的日子,有贼心不死的白日梦:“只是插满彩旗的城市/像极了一场多年以前的沦陷/当在春熙路的人流中低首/我怀念妻子、诗歌和自由的生活/——只是和字可以省略”。(《三月二十六日:糖酒交易会》)
三、“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显然他的诗,有太多的伤痛、太多的忧愤。
且看他对一个“敏感词”的纠缠,“永远都记得,历史的伤口”:
1995年5月,听崔健《最后一枪》写《结局》。1996年“六四”七周年,写《6月4日:新长征的路上》、《6月4日:最柔荏的时分》、《6月4日:牺牲》。1997年,写《六月四日:致受难者》、《六月四日:致流亡者》、《六月四日:致幸存者》。“重生”后的2009年,写《6月4日:出埃及》、《6月4日:加低斯的旷野》、写《6月4日:复活》。2012年“六四”23周年,“写给柴玲姊妹和王丹先生”《圣弗兰西斯和狼》。2013年5月,写《这一代的怕和爱》。2014年二十五周年,写《日历:第二十五年》、《流水:第二十五年》、《屠杀》、《广场》。6月5日被传唤回家后,写《罗马书》。2015年6月4日,在派出所讯问室写《那日子》。次日写《他们会毁了更年轻的一代》、《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随后又写《我想你,却不能说出你的名字》、《致青春》,还有在读六月诗集后,写《哦,你不要往东方去》。刚刚过去的2017年这一天,写《小史诗:廿八年》……
毫无疑问,这位当年的高中生太放不下。且看1997年《六月四日:致流亡者》:“为什么令我心痛的总是记忆/一个在叙事诗中人淡如菊的自我/生命承天而降。空遁而去/我们书写或被书写/爱与被爱。屠杀或被屠杀/剥削或被剥削/人子是金字塔顶端的祭物”。《流水:第二十五年》之一:“二十五年来/吃是一种缠绵/饮是一种哭泣”。之七:“二十五年来/生活充满了关键词/汉语都疲倦了/载不动/天安门的母亲”。之十一:“但在这个国家/你必须哀嚎/又在哀嚎中忍耐”。2015年《诗人不可能不想到政治》:“看哪,有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有人用了漫长的一生”。的确用了漫长的时光。他为何如此这般地“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他声言“‘六四’对整整几代人心灵的影响和精神的宰制,六四之后,多少人的灵魂就从此活在一个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可在信主之后,怎么还交不出、放不下?为什么在信主之后写出了更多的诗?
我想其理由,有些是心理的、有些是伦理的。前者如2014年6月1日所写《六月(组诗)》之一《如果》:“如果。我从来没有哭泣过,特别是夜里/那么当阳光爬上我的肩头//我不适应光明。不知生活如何继续/除非你使我的泪水,将床榻浮起”。后者如2015年9月《小哀歌》坦白:“有限的事物,在一瞬间被记忆改变/但我需要反复诵念,避免遗忘/多么难啊,保持对语言的忠诚/在忍不住呻吟和叹息的时候”。如果说后者是一种“记忆的政治”,则前者又通向一种“属灵的政治”。就像他所看见的:不仅“当队伍在街头被驱散/一个纪念日如期来临”,而且“枪响之后/福音就进城了”——
屠杀
你在血泊中遇见我
野有蔓草
淹没了足踝
风马牛不相及
你却动了爱情
我搭在你的肩上
田园将芜
追兵如水
从破裂的金罐涌出
三轮车,平板车,自行车
人民的脚惊慌失措
有人将诗歌挂在腰上
有人在汉语中大病一场
有人一边哭泣,一边艰难地说
哈利路亚
——显然能够指出,王怡的“六四”情结、“六四”书写与别的诗歌同仁的一致性,如果有心的话,也不妨把王怡的诗与孟浪主编《六四诗选》进行“互文与对话”的研究(就举一例:《哦,你不要往东方去》对廖亦武《大屠杀》有呼应)。我想那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这里,更想强调一位基督徒诗人的写作所具有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同一位写作者在“重生”前后所呈现的差异。如果说此前的王怡是“活在一个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则他信主后确认了“人子啊,历史的主人”的原则。他认识到“人从历史中出来/转身,又走进去”的荒谬,觉悟到“一个丑陋的世界/活在历史的坎陷中/我们在其中耕耘多年/但在我看来,一切都是徒然”。而喊出“哈利路亚”:“二十五年了,我们撕去青春/和诗歌。如嵇康撕去和世界的友情/恋人撕去负心者的蜜语/但没有爱,恨就永远活着/没有恩免,公义就必撕去/幸存者的二十五史”;“诚哉,我的主人/如愿以偿地,蝉/成为化石。树成为火焰/历史成为一句漫长的阿门”。且看今年所写《小史诗:二十八年》后半段:
每年我碰见一群人
他们说,还有多久,还有多久?
每年我碰见另一群人
他们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二十八年了
我不知道还有多久
但我知道你在哪里
我不知能否赶上最后的晚餐
但我相信没有一天是被浪费的
整整二十八年了,主人
世界是我的集中营
我是世界的集中营
但到底谁会先消失呢
他们,还是我们?
整整二十八年了,主人
活着,活着
活着就是等你宣布答案
总而言之,“知道你在哪里”,“等你宣布答案”。就像他2015年所写《我偏不去问还有多久》:“我偏不去问还有多久/何地,何人,何种方式/我惦记着一种预定/对我来说,生活必须神秘”。此种辛波斯卡式的诗句,表达了一位基督徒徒有的立场。注意到一位网友留言:“我读出了感伤,更有喜乐。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在哪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人在那儿。”当然看到网友留言:“我是基督徒。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总去纠结那件事。”作者回复是:“你真好,有主赐的平安。可以怜悯那些不平安的人。”
四、世界向左,灵修向右
重生前的王怡,写了许多个人主义的纪念诗。如1994年12月26日,“写给蓉儿21岁生日”;结婚两周年写《幸福是一把温暖的枪》等。翻阅《秋天的乌托邦》,会发现以日期为题的诗竟有四、五十篇之多,捡拾个人生命中的“飞鸿踏雪泥”,可见对个人生命与尊严的看重,也可见有情世间的一往情深。形成对照的是他信主后,写了大量“小诗史”:
《小史诗:9月19日》,《小史诗:坐牢》,《小史诗:9月20日》,《小史诗:9月22日》,《小史诗:在中国》,《小史诗:在成都》,《小史诗:在香港》,《小史诗:死城》,《小史诗:死亡》,《小史诗:9月28日》,《小史诗:在佛山》,《小史诗:早餐》,《小史诗:预备日》,《小史诗:在台北》,《小史诗:辜鸿铭》,《小史诗:史蒂文斯》,《小史诗:在泰国》,《小史诗:礼拜天》,《小史诗,或三一主日》,《小史诗:在纽约》,《小史诗:在美国》,《小史诗:在普度》……
就随便摘录一点吧。《小史诗:9月22日》之二:“文革末期。政治犯李九莲/在狱中题诗:/‘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响,/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小史诗:在中国》之七:“在中国,喧哗时常上升/知识分子。仿佛在火焰中燃烧/但一直没有凤凰从他们中间飞出来”。《小史诗:廿八年》:……
必须指出的是,他的集中许多诗不以“小诗史”归类,其实也差不多。如《逮捕夏天》:“他们逮捕了春天/现在。他们又逮捕夏天/他们逮捕了父亲/现在。他们又逮捕少年//
他们逮捕了麻雀/现在。他们又逮捕鸽子/他们逮捕了文字/现在。他们又逮捕语言……”;《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北方垄断了地位/南方垄断了金钱/你在沉默中倾听/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而我的缺乏/正是我最大的富足//哦,请把手伸给/一个不在身边的朋友/把忠诚献与/一个流亡者的政权//哦,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上帝最好的教练……”
——我以为这个大类的写作,是当年“纪念诗”的继续,何妨说成它的更新换代版本。虽然也还是历史事实经过个人心灵过滤的“心灵咀嚼史”,可能诗人主观上也还有为历史留真的见证文学用意。须要指出的是,就像一切伟大的见证文学一样,“史家之笔”还包含着“医家之心”。哪怕他的处方我们未必接受。看《望神止渴(十则)》之六:“将来若不成为现在,/过去的一切啊,就无法过去。//我再说,/不是医治过去,释放未来,/是只有未来,才能医治过去。”之七更是虎狼之药、电击疗法:
好比一个人,裹着棉衣,在雪地里徘徊了几千年。
这棉衣保存了他的性命,也扼杀了他逃离雪域的心。
所以,为了让他相信春天,只好先毁去他的棉衣。
——这是尉陈讲的一个故事,叫《中国近代史》。
该怎么说呢?正像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讲:“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也像我们的诗人自己早已挑明的:“只有非集体主义的诗歌,甚至非集体主义的语言,才可能从中诞生真正自由的批判性。但诗歌中的批判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拯救社会。”世界向左,个人向右。学者和批评家张闳说王怡的诗赓续了《诗篇》和智慧文学的伟大传统,我以为看得很准。就往这方面说一下。
智慧文学的影响是显然的。诸如《带着忧伤的思考》之四:“今天是原告。昨天是被告。/一个智慧的人,应当假定昨天是正确的。/今天。今天必须负起举证责任。”之七:“上帝啊,/只有你的百姓难养,/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默想十四首》之十:“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哲学家呢,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毒药/让苏格拉底受审,饮鸠/哦,活着是一种技艺/是不断壮大的,侏儒的身体……世界进入了无聊状态/凡有气息的,都爱自拍”。《夏日默想》之九:“应当提前哀哭,推迟喜悦。/因为喜悦和尘世一样短暂,哀哭如将来,一发不可收拾。”之十:“跪着祈祷,比蜜更甜。/站着思想,比金子可羡慕。”是他个人真实的体验吧?之十一:“意念纷乱,不是丰富,是贫瘠。/言语柔和,不是艺术,是恩典。”《对话练习(二)》之三:“用诗句谋害生命,是一大发明。”之五:“智者说,/以恰当的方式背负行囊/你将变得轻松/你若信,胯下会出现一匹骏马。”
理解这些并不容易。可我能否提醒自己说:拒绝读是不明智的?虽然我可以说,包括《圣经》里的《箴言》,整个智慧文学对缺少智慧的我是缺乏吸引力的。虽然有些很迷人:如象“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记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吧(或作不能自辨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辨屈。”……大概整个“箴言”、“训诫”的写作,在偏狭的我看来更像说教。看到在国外学术界,“在‘智慧文学’存在之合理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采用‘说教文学’(英文didactic literature)这样的术语,以取代‘智慧文学’。”(李宏艳《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研究综述》)我是有共鸣的。所以谈不深入。
想强调指出的另一类,就是一般非基督徒的中国读者会感到陌生,接受起来有难度、容易滑过去、但或许对作者而言更重要的写作,就是“灵修文学”。所谓灵修,据我粗浅的理解就是《诗篇》第一首中的“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灵修文学即以诗歌纪录自己的灵修过程。可以说是灵程札记,一种内向型的、沉思式的写作。据王怡自己说:“灵修意味着将一切复杂混乱的人性经验,包括创伤、痛苦、怀疑、否定,乃至一切病态,都完整地和个别地献给基督的一种生活方式。”“灵修是一个使知识受伤的过程。……大胆地,冒险地,和不顾情面的。因此,灵修总是笨拙的,和艰难的。(《关于灵修的默想》)
且看《神秘的哀悼者》、《变老的时代》书名,以及流水账般的篇名:《晨祷》、《思念》、《9月11日:查经》、《读书笔记:看透》、《11月17日:箴言》、《谢饭》、《默想(三则)》、《听道:浪子的比喻》、《12月8日:圣灵》、《夏日默想》、《默祷》、《天父世界(短歌集)》、《受难周》、《8月8日:晨更》、《默想十四首》、《晚祭》……我得承认,即使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懂得只有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的道理,也认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30:15)……读的时候力不从心:
这是正在变老的时代
死去的人即将回来
在一个新鲜的日子
大爷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
深陷其中,我们的罪孽
伐木机嗡嗡作响
小丑和观光客都不再年轻
悲伤的生活,继续绵延
那个有些口吃的男人开始沉默
有些还是能懂:“罪是公开的秘密,在我身上/有茁壮的身体/在厨房哼着小调/哼着,哼着/想起了一生中难堪的事”(《信心》);“我给了乞丐两块钱/是为了避免/去看他的两只眼睛/我去了灾区一天/是为了避免/在那里住一辈子”(《敬畏(短诗八首)》之《施舍》)。“诗人刀哥说/今天他拥抱了父亲/说:亲爱的,我爱您!/然后,彼此都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主人,现在我只剩下语言》之十三);“多么严重的倦怠期/基本上什么事都不想做/我的心遗落在未来/我跪在地上的时候太少/我的膝盖太硬,信心太软”(《回忆》之四)。有些经过思索也能懂。《神秘的哀悼者》之三:“成长意味着/把一些愿望留到以后去满足/去远方要带上鞋,钱包,和眼镜/去更远的远方,必须带上灵魂/和悔改的泪水”。
有些却不好懂。像《罗马书》:“世界的本质。不在形而上的命题中/快翻开报纸,浏览微博/恩典被困于现存的时间/惟有哭泣,祈祷和沉思/能击碎玻璃之门”。《如果就这么死了》:“如果就这么死了/没有我,会想起我/甚至没有一个我,值得被想起”,以及《我不知道什么,除非我先存在》:“真正的胜利,酷似一场失败/真正的荣耀,显露在卑微和人的藐视中/真正的生命,在必死无疑的地方//在那里,唯一的诗歌是祈祷/唯一的春天是冬天。比雪更白……”我想读不懂是很正常的。假如没有站在边缘,怎能读进他过去《一切边缘之上》?假如不是站在基督所站之地,又怎么读进去今天写的《站在基督所站之地》——“在那里,灵修即政治/因为最公共的,成为最私人的/最私人的,成为最公共的……”读不进去是很自然的。那是我“听众的耳朵也没有开通”。再说即使读《圣经》,我不是至今还有许多“不明觉厉”么?像“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样的异象,又能领悟多少?
但是也想鼓励自己。就选一首自以为能读进去的,完整抄在下面:
默想十四首(十一)
承认吧,我的一生都被算计了
魔鬼知道我出生之后的所有事
它先于政府,拥有摄像头,和大数据
它总是抢先一步,赶往案发现场
在我泪水下落之前,就设好背景音乐
承认吧,我的一生都被算计了
我的小意志,像泡泡糖一样扩张
又像垄沟的水,在渠道里随意流转
有人栽种,有人浇灌
但万物总是在睡觉的时候生长
那又如何呢,我的一生都被算计了
像野蛮的春天,爱是不由自主的
风是无中生有,又无孔不入
我在某个时候想起你来,或不想起你
在不想哭的时候哭,在发言的时候口吃
那又如何呢,我的一生都被算计了
那件毛衣什么时候买的,已穿过十年
什么时候破一个洞,什么时候你补好了
而我向你发怒的每一个字,在小学一年级
都工工整整地抄写过二十遍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吗,我的一生都被算计了
有一位天使知道我出生之前的所有事
也知道我殒灭之后的遭遇
这一切使我和你挨得更紧,像那些声音
从上帝的口中出来,又回到上帝那里
五、“执我之手,与我偕亡”?!
现在开始,“对话练习”,说说你的短板。
作家北村说你,“饮苦水、唱雅歌”。我倒觉得,你唱雅歌无能。
或许不是无能,而是极其特别。只是以鉴赏水准,感到不可思议而已。你一直强调雅歌。作为牧师布道讲:“华人教会,一般特别强调《雅歌》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轻易地跳过《雅歌》在字面上刻骨铭心的的男女情爱。”“我们需要福音,我们也特别需要《雅歌》这卷书。”作为批评家,“重新发现了台湾民歌时代的音乐大师梁弘志……19岁即写出不朽曲目《请跟我来》,一鸣惊人。他将福音与爱情完美结合,堪称当代汉语中的“雅歌”——可是作为诗人,你的写作很奇怪。
相对少,也平平。像写给妻子的《感怀》,另外《8月24日:婚姻场景》,为钟昊何娟夫妇结婚十周年及婚姻更新礼拜所作《9月23日:月亮忘记了》,《婚礼:送给郄弟兄和邹姊妹》,《婚姻》……总觉得是劝勉诗。就算正确,干巴巴的。然后就是,若干首“爱到成伤”的诗:读经时写的《6月12日:先知西番雅》,有点阴郁。《爱是对我的一种威胁》写:“如果不离开时代,就不能和你在一起/如果不能在超市的入口遇见你/我将死于世俗”,还需要分析,目前觉得怪怪的。《失乐园(组诗)》之八写:“比死更可怕的/是走向死亡的时候/失去你。我的爱人/你决定了吗/执我之手,与我偕亡/谁能说这不是最浪漫的事”,给人感觉像“刑场上的婚礼”。《他在婚礼的颂赞中睡着了》也是:“他在别人的欢乐中睡着了/在自己的欢乐中惊醒/他终于发现有一种欢乐/比死亡更坚强/比新娘说出誓言还要紧张”。
或许我要调整一下心态再读。或者在审美更新以后重新打量。迄今为止,你的雅歌要不平平的,要不过于硬语盘空,好几首给人某政治人物“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联想。对照重生之前、还在书写哀歌的你,变化确实发生。就是那时世俗夫妻,冷里面有热。现在“清教徒主义”,极热中有冷——不知该怎么表述,就直接展示。前面说了,重生前的诗人,曾“把哀歌当雅歌”,可是无望中有情。献给爱情的诗如《情种》、《乞求》、《初吻》、《幸福是一把温暖的枪》写得何等好。《乞求》:“一枚圆月浮上夜空/犹如清水煮蛋/我们在宇宙的一个瞬间生活/手拉手。让血液流到指端……/等到清晨醒来/我们发现自己紧握自己的手/仿佛在梦里祈祷过什么。”读来令人心动,接近《雅歌》故事。我还要要说,甚至《风月之夜》的美艳也可以面对,无论如何它诉说着更大的信息……可是受洗后,诗人作为牧师,就放不开了。或太“一往无前”:
小要理(组诗)第82问
云怎样被风爱着
风怎么吹,云就怎么动
鱼怎样被水爱着
鱼在水里面,水也在鱼里面
但我这样被你爱着
我却是一个背叛者
你说往西,我就往东
风若掉头
云就要落成雨
水若干涸了
河床就是鱼的坟墓
但你却为我落成雨
但你却为我走进坟墓
容我再一次讲,这样诗不是不好,单独看可喜得很。但若拉通来看,动不动“爱进坟墓”,养成了“执我之手,与我偕亡”的王版浪漫模式……就让人有点郁闷。干吗老把爱跟死联系起来?难道不是一种奇怪心理?当然也有一首将“柴米夫妻”上升成“神仙眷侣”的诗,“若得山花插满头”一般质朴喜人,就让我专门把它抄录下面:
小史诗:早餐
那个每天早上喂养我的女人
用鸡蛋哄我,用打折的外国牛奶饮我
和我牵手祷告,在那一瞬间
令我感到,唯一的缺憾就是
没有立刻在这样的早上死去
那个每天用粮食和语言喂养我的女人啊
只是今天早晨,吃着茄子饼,和药丸
主人啊,我忽然明白
你把这个女人给我,不是为今生
是为来世。不是全部
是一个开始
——当然诗中也提到死,结尾注目来世,已经好多了。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话题?可能有几个层面的思虑:一是站高点,都说中国现代文学“冷硬荒寒”,为什么会那样。如果人心苦,雅歌写不出。所以生命更新后,若在“福音与爱情结合”方面薄弱,在我来看还是一种“严峻现实”。二是诗人成为基督徒,进而成为牧师,写雅歌时会不会发生“角色冲突”?也是一个我关注的问题。约翰·多恩有《艳情诗与神学诗》,好像受到争议。约翰·多恩写《艳情诗与神学诗》,究竟该怎么看待?梁弘志写作心态轻松,可他不是牧师……尤其是长期“有爱”环境中的诗人,跟“爱比死更冷”的我们,岂可同日而语?
但不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吗?怎么这个题材这个领域,表现不够“全新”?是否也属于你所讲的:“我个人以为审美观的更新,可能比人生观还更难、也更靠后一点。生命仿佛刹了车,但内在观念及审美体验,总要再往前冲一段……”(《信仰与审美》)的情形?也包括为了“彻底决裂”,不惜矫枉过正地“英雄主义”,动不动就“刑场上的婚礼”……我怀疑那是某主义,不是我们要的生命。是小孩子家家动不动“爱到死”。信仰上事,不容我说。可说到诗,觉得《与神亲嘴》真是一本雅歌的名字。其中也该包括,一首“难过得”蓬头垢面的诗: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最近太多事情,令人窒息
请让我软弱片时
在黑暗的房间禁闭片时
像那些被带走的朋友,在夜里
哦,和耶稣一样,在夜里
穿过变得野性的城市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等待欢乐,欢乐的袭击
但不要用咳嗽打断我
不要转换话题,只要几分钟
手机静音,快递也不要来敲门
我必须独自面对,灵的窒息
如果世界刚好在此时坍塌
如果有重要的人物离世
哦,愿这一切,仿佛无事发生
因为我难过得就像
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容我不洗脸,不梳头
不肯出来见你
为了积蓄泪水的决堤
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吧
为了让光明更加刺眼
为了让我千百次地排练
你推门进来的那个瞬间
六、哀歌是否还能唱?
最后一个问题,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理论。
想质疑你对“哀歌”的偏见。主要不是对他的诗,而是对他的鲜明观点。毫无疑问,你作为理论家与批评家,在《信仰与审美》、《作为救赎的诗歌史》等重要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洞见,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能截断众流地让人有所警醒。但是也有偏失。
想批评的观点,最先出现于《作为救赎的诗歌史》一文中:“……只有两种诗歌,一种是哀歌,一种是赞美诗。后者是我不曾了解的。也是大多数汉语诗人不曾了解的。哀歌是无神论者的救赎,是挣扎在审美与信仰之间的救赎。哀歌在本质上是渎神的。”“哀歌是我作为罪人的史记,作为忏悔者的口供。……因为生命在哀歌中没有前途。”完善于后起的《信仰与审美》书简中:“人类的诗歌史有两个极致,一个是哀歌,几乎最好的诗人写得最好的诗,都是哀歌。……另一个是赞美诗,在我看来,圣经中的《诗篇》和《雅歌》是神人合作的永不可逾越的人类诗歌的极点。而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则是圣经以后人间诗歌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次点。”根据我的阅读,你的分类的确有认同者(如齐宏伟《信与诗》)
我想对个人而言,决心“从哀歌开始,到赞美诗结束”,别人无可非议。可是作为一种理论,总觉得是大有问题的。容易形成误导。就忍不住提出质疑如下:
一是作为论断,说“哀歌在本质上是渎神的”,怎么解释《耶米利哀歌》?还有就是概括“赞美诗的极致是《旧约·诗篇》”,是不是以偏概全?一个基本事实是,《诗篇》一百五十首固然多赞美诗,可也有别的啊:有137篇那样的哀歌,有42篇那样灵性低潮的诗,甚至有88篇那样的咒诅诗……若按特伦佩尔·朗文、雷蒙德·B.狄拉德《旧约导论》的说法:“(《哈巴谷书》)先知以哀歌的形式在上帝面前抱怨,与哀歌式的诗篇近似(诗6,12,28,31,55,60,85)”,那些“哀歌式的诗篇”属于你“赞美诗”范畴吗?实在疑惑。
一是作为“渎神哀歌”的对照,你断定“赞美诗……是大多数汉语诗人不曾了解的”,我其实懒得反驳。是没有心情。理解你“破中有立”,可是我能否直截了当讲:由于“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之类太威武,很多人败坏了胃口不想“改口再赞美”。甚至它使许多人丧失了真正信仰的能力……或许你或纠正,那是“伪父临朝”啊……是的是的,我都承认。但是我想“抬杠”的是,从文体、类型或主题的角度,断言“大多数汉语诗人不曾了解赞美诗”,不是太武断太性急也太雄辩了吗?
你其实没有限定,也没有展开说明。但如不能回答疑惑,再强势的话语也只有“自说自话”。我想继续质疑说,从国外来讲,正如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10版)》阐明:赞美诗通常用来指赞美上帝或表达宗教情感的歌曲,但也有有关世俗乃至异教主题的“文学赞美诗”。比如19世纪出现了像詹姆斯·汤姆逊的《四季颂歌》、济慈的《阿波罗颂》、雪莱的《阿波罗颂》《潘神颂》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赞美诗中的后三首,像原先许多希腊赞美诗一样,都是献给异教神明的。”从中国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起码从《诗经》时代开始,一种“颂”的文体或精神就赫赫炎炎、光焰万丈,它“使审美局限于歌功颂德的载道巢穴”(刘晓波),连同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宝座崇拜”一起,构成我们这个民族积重难返的精神传统(我案头就有一本书,胡吉星《文体学视野下的美颂传统研究》)……哪怕咱们再不喜欢,问题都不易解决。
其实我能理解,你的义无返顾。“那时我们喜爱黑暗,对忧伤/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贪恋”(《哦,那令人喜闻乐见的,死亡》),可现在,实在不想回去了。而且我也理解,你的某种冷峻。面对“哭不出来的时候,有催泪弹”的现实,“伤心过后/有人把爱另存一种格式……只是哭的人多/悔改的人少”(《低潮》)的确让人不好说什么。再加上你对昆德拉“第二滴泪”的警觉,你在一篇文章里深恶痛绝地写:“有泪可流也许是善良的,甚至是美好的。我们若不流泪了,就会慌张。觉得自己的麻木无可救药。所以我们若哭泣,我们似乎就对人性保全了信心。然而,麻木是一个深渊,眼泪却是更深的深渊。我们在麻木中卑微下去,在眼泪中崇高起来。这不过是人堕落的两种方式而已。……于是我做了一个祷告,祈求我的神拿走我的眼泪,也拿走我内心的恨意。”(《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
——对于“祈求我的神拿走我的眼泪”,我要表示个人的尊重。虽然在同一文章中,你也点赞了“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甚至提到“曾经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哭了。……为我们的罪而哭,为我们一直伏在死亡的权柄之下而哭。我们若不认自己也在世界的罪当中,就轻易把自己的眼泪当作了耶稣的眼泪。把我们心中对罪的恨恶,当作了上帝的忿怒。”你的自我提醒很重要,我们的眼泪并不洁净——可我们的歌唱呢?怎么觉得同样是世界的罪人,你更强调“喜乐”,“喜乐”是“政治正确”,不喜乐会逃不了“渎神”的指责……可你而对哀哭一直很防范。让人觉着“左比右好”,“喜乐”比“哀哭”属灵。
我的感觉对吗?不敢有把握,只是很疑惑。
然后从实际说,其实你也有哀歌。重生后的写作中,篇名“小哀歌”的只有两篇,有些我以为是不叫哀歌的哀歌,是违反了自己理智的哀歌。比如前引《屠杀》头三段,不象《耶利米哀歌》开头又是什么?再如《小史诗:死城》,也是典型的哀歌。前两节一写1624年大明将亡,一写1948年长春围城,都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第三节写“巴比伦大城,也要这样倾覆//哀哉。哀哉。一时之间/她的灾殃一起到来……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要在这废都中被看见了”。作为对“巴比伦大城”的诅咒实在水到渠成。还有《小史诗(两则)》之《观音土》,从头到尾都是“哀哉!哀哉!”的笔调:
观音土,即白泥
含大量氢化铝
颗粒细腻
感觉极像面粉
但没有一点粮食成分
连动物都不吃
史载,1959年春
四川许多地方的老百姓
开始进食观音土
食毕,有饱足
终究饿死无数
对那些不相信永生
又不能免死的人们来说
我们岂不是吃了一辈子观音土
终究,和光同泥
归于尘涓
虽然是“春秋笔法”,只有极其克制的点睛式议论,可是强烈的情感力量使人不可能不把它当成哀歌。可是有的诗就值得推敲了。像《11月13日:献给自焚的唐阿姨》一诗结尾:“可是拆着拆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要来了”。读了几遍都觉得很怪。“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要来”是好事啊,可前面几节明明是令人悲愤的事。“跳转”太突兀,有一点“悲欣交集”……可能是我的理解有问题。毕竟整首诗用了亚伯拉罕置办“产业”和以撒换个地方挖井的隐喻,你想说我们在大地上是寄居的,“不动产是多么荒谬的词”……总觉得你的安慰很奇怪。总觉得跟唐阿姨自焚的事不怎么搭调。甚至有“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碱上倒醋”之嫌疑。
我的感觉对吗?不敢说是对的,只是很疑惑。想不清怎么回事。
是否唱哀歌,就是不属灵?是否太难过,就会有问题?涉及到的神学是非我不敢置一词,“审美没有被审理”我也是承认的。可是我就是喜欢下面一首“软弱”的诗: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最近太多事情,令人窒息
请让我软弱片时
在黑暗的房间禁闭片时
像那些被带走的朋友,在夜里
哦,和耶稣一样,在夜里
穿过变得野性的城市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等待欢乐,欢乐的袭击
但不要用咳嗽打断我
不要转换话题,只要几分钟
手机静音,快递也不要来敲门
我必须独自面对,灵的窒息
如果世界刚好在此时坍塌
如果有重要的人物离世
哦,愿这一切,仿佛无事发生
因为我难过得就像
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容我不洗脸,不梳头
不肯出来见你
为了积蓄泪水的决堤
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吧
为了让光明更加刺眼
为了让我千百次地排练
你推门进来的那个瞬间
7、一切还未成为事实
想说的没说完。文章要有结尾。
可是我已吃力。还是以王解王:
正如火星总要向上飞动
正如火星总要向上飞动
你给我的祝福中,包含了受苦
我的诗句是伟大的残篇
隐约着,一种他们没有想过的可能性
一旦超自然的手经过这些句子
喔,我的作品,将使荷马也显得猥琐
我的字缝里,包含了,折叠起来的空间
隐含着另一个,失踪的宇宙
只等这一切成为事实
就像芥菜籽成为巨木,一点酵使面团发起来
我的三流的文字,将迸发惊人的壮丽
是的,这一切还未成为事实
因为我还没有死,没有经过坟墓
目睹精灵,在语丛中起舞
况且我死了也没有用
因为世界还未绝迹,未亡之人还在哭泣
审美没有被审理,听众的耳朵也没有开通
而读者呢,哦,他们都是罪人,自以为是地
欣赏牛粪的纹路,厌弃愚拙的信心
正如火星总要向上飞动
你决定到那一天,给我完全,所以我现在不完全
给我公义,所以我显得虚伪
给我美,所以我的句子不忍卒读
奖赏,奖赏。你给我的奖赏
包含了七十年的失败和羞耻
2017年6月4日初稿
2017年6月12日定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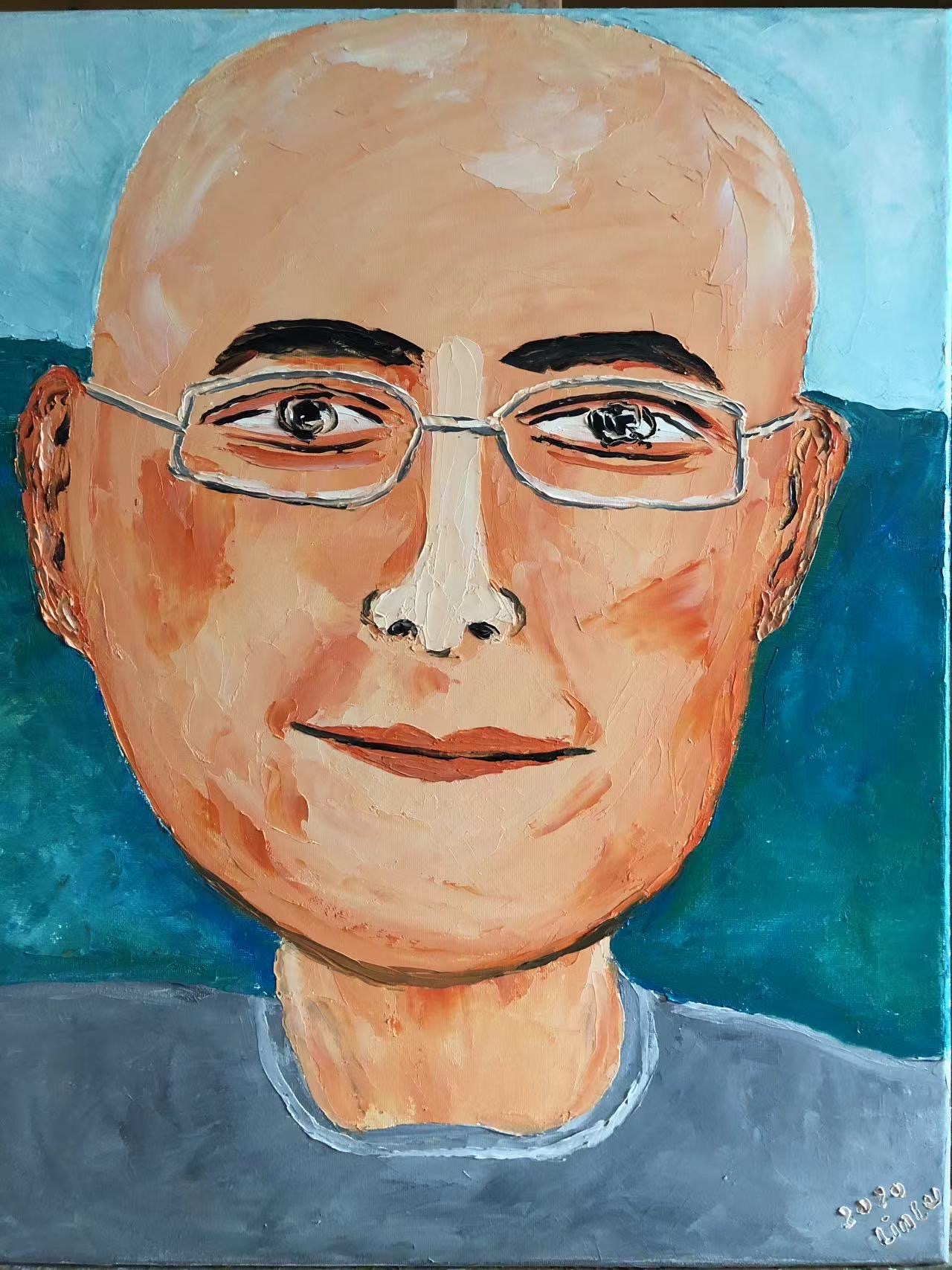
本文作者李亞東畫像。

